19 阿伦特II:怎么才能不变成坏人?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来和我一起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上一讲我们讲到,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是丧失思考能力的结果。这个诊断看上去很简洁,但细究起来,会带出很多麻烦。比如,人怎么就会丧失思考能力?丧失的是哪一种思考能力呢?等等。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很多争议,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思考”和“善恶”的关系,这也成为了阿伦特生命最后十年中反复求索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是一条崎岖的道路,每提出一个回答,又会引发出新的难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阿伦特有一个计划,就是写作《精神生活》三部曲,第一部是《思考》,第二部是《意志》,但她刚刚开始写第三部,就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人们发现了留在她打字机上的最后一张纸,纸上只有一个标题:“Judging”,意思是“判断”。可惜她永远无法完成这部著作了。
但这个标题正好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阿伦特的一个线索。 在我看来,阿伦特最后思考的一个关键要点就是“判断”,更准确地说,是“独立判断”。 就让我们把这个词当作火把,跟随阿伦特走过这段思考之路。
为什么说艾希曼“丧失了思考能力”?
首先,阿伦特为什么会说,艾希曼“匪夷所思地丧失了思考能力”呢?要知道,艾希曼当时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甚至引用康德的名言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是履行职责、服从法律,因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的命令是当前法律的绝对核心”,所以他艾希曼不仅是服从法律,而且是让自己的意志与“法律背后的原则”得到了统一,这符合康德的哲学。
这种口才,恐怕会让很多不善辞令的人深感自愧不如,那么阿伦特为什么会说艾希曼“浅薄”、“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阿伦特的意思,并不是说艾希曼愚蠢,或者说他是在撒谎,而是说 艾希曼满嘴都是套话,让自己陷落在陈词滥调之中,又把这些陈词滥调当成自己的盾牌和武器,用它们来抵挡现实,拒绝真正的思考和对话。 艾希曼虽然能够引用康德,但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引用简直“令人发指、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康德所讲的道德,恰恰是和独立判断密不可分。
这里我们就发现, 阿伦特说的思考能力,实际上是积极思考、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去做出自己是非对错的判断。
为什么独立判断很重要?
现在,人人都会宣称独立判断很重要,这本身似乎也成为套话了。但你是否明白,独立判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阿伦特的回答是, 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
阿伦特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德国最早支持纳粹兴起的人群,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边缘人群,而是像艾希曼一样,是有文化、有教养的所谓“值得尊敬的人们”。正常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去犯罪,因为“不能杀人”是公认的道德法则。但是,纳粹建立了新的法则,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那些所谓“值得尊敬的人”竟然很容易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在阿伦特看来,大屠杀的灾难表明,旧有的道德模式已经失效了。传统的道德学说着眼于习俗、习惯和规则,道德教化就是让人循规蹈矩,能遵守道德规则就是有道德的人。但20世纪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传统的习俗和规则完全可以被颠覆。在纳粹德国就出现了这种新的现象:人们依法作恶。
这里有一个极为严酷的道德困境: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作恶,如果想要行善,却可能触犯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道德和教化变得自相矛盾。 所以阿伦特发现,道德的真正涵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自己独立做出关于是非对错的判断。
为什么独立判断又很困难?
好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案听上去好像没什么深奥的,很清晰,但实际上却极为困难。
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但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就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所以,盲从当然不行,但你独立判断,就一定能做对吗?谁也无法担保。
结果, 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 。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你可以说“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辞,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完全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到独立判断呢?
独立判断,究竟应该怎么做?
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
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
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
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么哲学气质,也不怎么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
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 忠实于自己 ”,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 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 ”。 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 ,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乃至付出生命。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 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多么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就是moral integrity,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涵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德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他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自己的思考
现在,让我们回到阿伦特在临终时刻写下的那个标题,“判断”。独立判断究竟要怎么做?阿伦特曾经说,“就各种特殊情况作出判断而言,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 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
我自己阅读阿伦特的作品有近30年了,在过去15年,每年都要给研究生讲解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每一次我都会重读她的作品。我一直感到,阿伦特的思想非常令人着迷,也令人困惑,因为她的思考是未完成的、探索性的,从未给出完整的答案。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它要求我们,必须和阿伦特一同思考,必须自己来思考,如同苏格拉底那样,用思考恢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本质。
问答
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来思考:你有没有过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坚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后来的结果又是怎样?欢迎到评论区留言,我很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编辑按:第19讲的小加餐,刘擎老师已经发布在知识城邦。
第十六次小加餐,老师进一步辨析了阿伦特所说的“独立判断”究竟是什么意思。独立判断和个人的“任意”(arbitrary)的判断有什么区别吗?
在思考判断的依据时,“道德”和“良知”又有什么不同呢?
阿伦特看上去更倾向于以良知作为依据来进行判断,可是“良知”究竟又是什么呢?
刘擎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这个回答没办法用一句话概括,欢迎你亲自去看看刘老师的回答。请你→戳这里观看。
划重点
1、阿伦特说的思考能力,实际上是积极思考、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去做出自己是非对错的判断。
2、在现代,传统的道德和教化可能会变得自相矛盾。所以阿伦特发现,道德的真正涵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自己独立做出关于是非对错的判断。
3、独立判断究竟要怎么做?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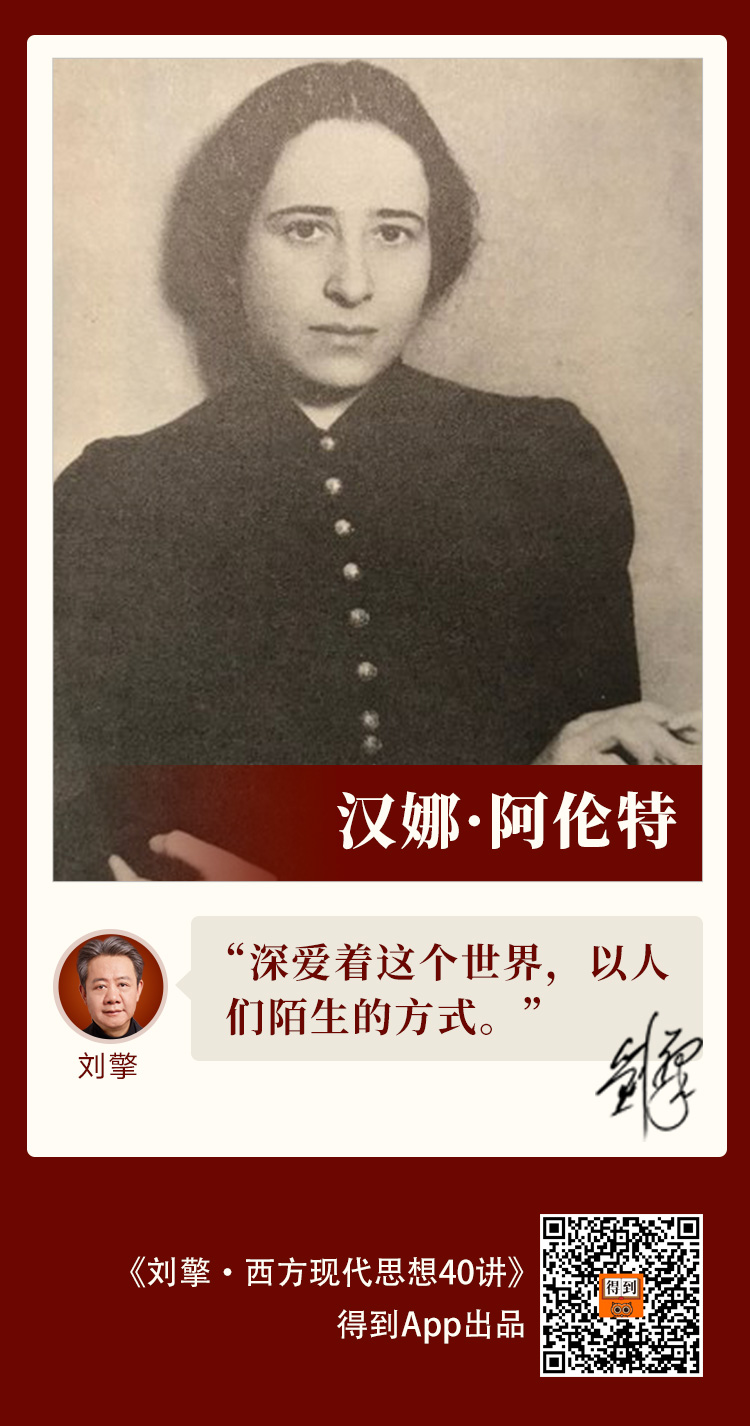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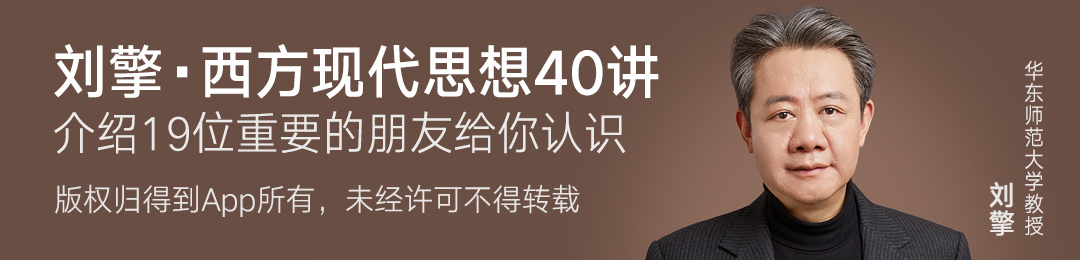
热门留言
伪装:你有没有过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坚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后来的结果又是怎样?
记得当时还在原来的单位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两次这样的事情。 第一次,我是旁观者。 当时我刚转回工程,做一个北方新建港口建筑甲方。 一位我很敬重的领导,在一座五万平米双层钢混仓库的建设中,无视上级压力,做出了一个工期不能抢,标准不能降的要求,导致理论时间仓库需要延期三个月才能交付,上级多次派人来视察,敦促,但都被驳回。 结果,在南方同时建造的,同样设计标准另一个仓库,按照要求抢工,结果在一个雨夜竟然一层屋顶倒塌,酿成数千万的损失,我们都很庆幸,但是那位领导反应很平淡,仿佛只是做了很平常的事情。 第二次,我是决断者。 那时,公司与另外的港口合资合作,我转入新公司,是唯一一个经历了建设期的工程人员。 当时新领导要求冬天抢工一片场地做矿石堆场,我极力反对,无果,无奈只能尽可能严格要求施工,但条件太差,根本不符合工程要求,我多次建议一定要留足养护时间,被无视,结果矿石一堆载,整个原本一马平川的场地就像是起了波浪,我直接被消失,不允许谈论这事,赶紧修好。。。 此后,这种被无视专业意见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每次据理力争,也曾经避免过更大的损失,但无论意见还是结果,都被人无视,终于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被无视还要承担责任的工作,裸辞离开。 现在回想起来,我只后悔当时学艺不精,专业知识不扎实,没能用我的专业能力击败那些不专业的作死行为。
佛祖门徒: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电影《肖克申的救赎》 自我想象一下,如果我现在是纳粹官僚体制中的普通一员,我是否应该忠实地执行指令?似乎服从才是正确的,即使有一闪而过的反思,仍然会认为我是按照命令做的,即使有错,我只是个执行者,不会把历史责任归咎到我的身上。更进一步想,如果所行正确,我是否应该更加积极努力工作,创造更出色的“业绩”呢?现在想来都有些可怕,做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有勇气照此行事是一件何其艰难的事。 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让我想起稻盛和夫先生的那句话“作为人,何谓正确”,我们永远不要丧失独立思考、判断和反省的勇气。
红燕:终于赶上进度,这真是一门灵魂唤起之课,单用喜欢二字忽觉如此浅薄!感谢刘擎老师,感谢得到,感谢我自己,庆幸没有错过! 我在环保行业工作十年了,去年十月离开了呆了八年的公司,离开的原因我到现在也不能完全想明白。离开前的一年多,我心态已经非常不好了,身体也疲惫到了极点,情绪很不稳定。我在原公司也算是核心技术成员,中层干部,无论是待遇职位和领导对我的重视程度,都很难在别的公司再找到。但领导越是重视我,我与公司的冲突就越大——我本是研发部经理,但由于公司近两年项目量少,加上行业波动回款困难,造成现金流紧张,生死存亡压力突显。于是我们部门成为了开源的主力,只要市场人员能找到的环保类项目,我们都号称能做,都经我手攒出来,然后配合销售卖出去。好像公司的生存,都赖于我抄袭的速度,都赖于我没日没夜的不懂装懂照猫画虎,都赖于我如何不露破绽的忽悠。然后领导对这个上了瘾,技术部门也开始全力加入。原来的论证步骤不需要了,经验也不需要了,严谨更是一种要被打倒的东西。 可是我们做的是工程啊,做不好轻则开不起来,重则会出人命的。更进一层我们做的是环保工程,是城市公共事业啊!我们为了生存,就可以如此随便的面对一件本应该严谨对待的事情吗?后来和领导的一次谈话,让我痛心无比,他劝我明白,项目根本就不是靠我们所谓的技术和产品拿的,你的那些方案不过是钱袋子的外皮而已。 但最让我感到痛心的还不是我们一家公司折样做,而是整个行业都在这样做,如果只是一家这样,根本就不可能奏效。我越来越觉得这像一场顶着项目之名的分钱盛宴!国家的钱不分白不分! 他们笑我看不穿,笑我太单纯,笑我太愚昧! 我离开时,总经理送我的忠告良言:以后别那么倔,那么实在,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至尊女宝:一个人只有在世界中获得与他人交往的经验,才能在思维中知道如何同自己进行对话。同样,真正的思维也不会在孤独的自我中产生,而是依赖于对它进行的公共表达和交流。纳粹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构造成一体化的组织,多元异质的社会以及个人被压缩进单一的结构。最后我想说——哲学课,至少要听两遍,太难了😰
Sencer:今日思考,以前的一位供应商,由于疾病突然的去世,我们单位欠了他一笔钱,业务的经手人是我。当时有一位其他部门的领导,不知道什么原因,与这位供应商有矛盾。他特意找到我的上级领导,不让付这笔钱,上级领导把事情推到了我这里。这个人又找到我说此事,我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因为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具体的事情。 后来知道了是这位领导与供应商的妻子有私人上的恩怨,就想着利用这件事情刁难她们。知道了什么情况以后,我心里也有了数。不知道是谁给供应商的妻子说,我是负责这一块业务的,她就找到了我,哭诉自己的丈夫走了留下一堆的白条,请我帮忙在单位给那些欠条证明一下,把钱付给她。并且还答应给我提成。我对她说忙可以帮,提成就免了,还告诉她也不一定能帮上忙,尽力吧。 其实我可以不管这件事情,但是出于一种内心的正义,决定还是帮助她。我找到了当时的主管领导,向他说明了情况,证明欠的钱是事实情况,又替她说了一些好话。 结果可想而知,钱很快的付了出去,得罪了那一个部门的领导,见面都不说话了。后来这个人居然又成了我的上级领导,现在的日子可想而知,时不时的会给我穿个小鞋。也借了个机会把我调离了原来的岗位,其实彼此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在这一件事情上我觉得自己是做对了,而且还会用自己的道德评判去做事,相信自己出于本心的选择是正确的。虽然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为了保住那些失去的东西,而失去内心的良知,恐怕以后还会受到内心的谴责。
高军61221809:独立判断特别需要巨大的能量去独自冒险,并且承担责任。 大概率局面是付出的代价与得到的回报不成正比,趋利避害的人,选择恶的平庸顺其自然。
刘擎(作者) 回复:这取决于你说的“回报”是什么意思。
晚霞:周恩来逝世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大家流传一些悼念周总理的诗和文章。突然有一天召开员工大会,要大家交出一切有关周总理的文章,也包括悼念的诗歌,并要说明这些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有隐瞒者,大家必须向组织上揭发。 两天之后,年龄比我大一岁,跟我同是学徒的,一起吃饭,一起同进同出的“闺蜜”问我:“你师父不是也拿来了很多的诗歌给大家看吗?她为什么不交上去?你为什么不去揭发?” 我当时吃了一惊,真没想到她会问我这个。我认为我师傅没做错什么,我知道文革的厉害,最好是别提这事。 于是我就对她说:“上头要查的是从外面弄来的,我师傅是她自己怀念周总理,自己写的,不是从外面弄来的。再说了,你不是也怀念周总理吗?你也不是写过给我看过吗?大家都是一样的,以后别再提了。” 以后就没再提了,也没有什么后果。
巨石:想请问刘老师,苏格拉底的“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是不是和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不管外界条件怎么改变,都要追求自己内心的原则和宁静,哪怕被当作异类和不符合传统规矩也要有自己的一份坚持。
刘擎(作者) 回复:至少是很接近的吧
贾春叶:2014年冬,母亲病危,在大同五医院肾病科,医生第二次下了病危通知。我是老大,两个妹妹,弟弟最小。怎么办?他们都在问我。医生说肌酐太高了,需要做透析。考虑到病人的实际情况,要尽快去北京准备透析通道。此时,母亲心衰合并肾衰,还是三十多年的糖尿病人,一年前还感染了骨结核,苞饱受病痛的折磨。医生的建议固然专业,然而他们并不能感同身受,就连我们做儿女的,在她跟前侍奉这么久,都做不到。母亲到底最需要的是什么,恐怕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医生,父亲,弟弟妹妹们,都在等我的决定。我只能自己思考。我也知道,无论是怎样的决定,我都要承担全部的责任。与医生再次沟通之后,我决定说服大家,出院回家。之后不到两月,母亲安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后来父亲跟我说,我没有安排母亲在医院插那些管子做手术,他们很欣慰。花钱不说,更不愿意受那个罪。然而我要面对的是村里人对我有关孝道的考量。到底在医院尽到最后一分力是孝,还是顺应双亲的意愿是孝。因为大多数人选了前者,我们很另类。 第二年春天,有人给父亲介绍了同村的一位寡妇阿姨,希望两人搭伙过日子,相互有个照应。我们姐弟意见一致都同意了。有人问我,这么快就给父亲再找个阿姨是不是对去世的母亲太不孝了?我告诉他,去的已经去了,活着的却还要艰难地活着。父亲也有糖尿病,相比较之下,我更担心父亲的安危。我也想要孝敬母亲,但是现在,首先要解决父亲的问题。孝敬父亲是当务之急。后来村里有各种的议论,到后来是羡慕父亲的比较多。 所有的独立思考,都要承担责任,都需要面对新的局面。坚持最初的出发点,远离平庸的恶。
陈C:“恶的平庸性”的问题不在于不思考,而是不“主动”、“独立”地去思考。就像艾希曼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选择、执行,以及可能承担风险的时候不思考,在行动之后不去怀疑、反思,而只是在最终受审的时候才“被迫”地快速思考,为自己辩护。这样的思考显然是糟糕的,它只能带来陈词滥调与牵强的解释、辩驳。
有效的思考也许不是早晚这样的实际问题,它应该是时刻进行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应当思考什么,以及如何思考。关于思考的内容,价值观与道德就值得我们思考,具体地讲,我们做出任何一个选择,包括对善恶、高下的判断与重要的人生抉择时,应当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在我看来就是始终值得思考的东西。
最困难的可能还是该如何思考,尤其是该如何触发思考。从艾希曼的极恶,到施密特与卢卡斯基于独立判断的善,除了老师所讲的“忠实于自己”之外,另一个方向应该是去怀疑——怀疑自己的处境,怀疑自己的言行及其标准,怀疑自己是否遵从于内心。怀疑有时候很可怕,甚至可能会让我们陷入虚无,但怀疑也是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越是确信的东西越要留有怀疑的余地,能帮助我们免于堕落,尽可能避开歧路。
王黎璐:在工作中有过大家都觉得可行,而我坚持已见的时候,因为涉及到的领导同事很多,不适合讲太细,但是当时的压力确实很大。现在回头来看,恐怕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正确的,自己的站位不够,见识太窄。但我确实很希望自己的选择以自己理性思考的结论为依据,不盲从,即使被评为“固执、迂腐”。 还有一点感慨,阿伦特对于艾希曼审判的思考,探讨了人放弃主体独立判断,陷入到平庸之恶的问题,而对她的误解、指责和咒骂,不也表现出人们被情绪、舆论、民族身份等因素左右时,同样可能放弃作为独立个体的判断。“平庸之恶”并不只会以服从命令、循规蹈矩的方式体现,同样也可以体现在人云亦云、激愤于群情之中。
snowdragon:举了施密特和苏格拉底的例子,其实还是回到经典一元的善恶判断,因为他们两个人要吗是经典善恶观的典范,要吗是遵从了这种典范。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也就没有现代性的困惑了,即上帝已死,没有标准答案可以遵循了。另外牺牲个人去拯救别人就比保全自己拯救自己的家人一定更高尚吗?
刘擎(作者) 回复:你好,我是这门课的编辑。我觉得你说到的内容和提到的问题都很好,老师在这一讲的加餐(发在知识城邦)中有所涉及,欢迎你去看看,也许会有启发。
Lemon: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听着老师念来不禁潸然泪下! 保持觉知!有时真的很难,就像生活在水里的鱼,实时感知到水的存在,苏格拉底在临刑前告诫朋友“今后,你们还是要跟以前一样,按照你们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艾希曼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甚至引用康德的名言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是履行职责、服从法律,因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的命令是当前法律的绝对核心”,我们有时会说别人,啥都听他的,难道他让你杀人你也去?艾希曼难道真懂康德吗?他已经失去了起码的人性! 儒家这点说得特别透彻。孔子跟学生讨论问题,就会提到“你的心安不安?”孟子谈到人性的问题,就会问“你的心忍不忍?”“不安”跟“不忍”这两个词,是了解儒家的关键,它有个特色,都从“不”来说。孟子说人生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中武妖:刘擎老师,不作恶真的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事情,一件在大众看来的恶会被很多人解读,有的人会用平庸的思维来接受恶,有的人会用自己的道德来反抗恶,有的人会用自己的行为来战胜恶。前一节课也说过平庸之恶为什么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就是因为平庸会接受作恶的行为,在接受作恶之后坚持执行,在平庸看来恶只是接受的行为,自己和恶没有关系,恶是上级的指示。而在纳粹医生看来只要是对于别人的伤害就是恶,既然是恶就不应该被忽视,这才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这才是真正的不作恶的基础。 我有一次晚上看书的时候我母亲对我说,为什么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现在晚上开始用功了,你现在读书有用吗?我只好如实的回答,告诉母亲以前上学都是给你学的,现在才是给我自己学,我说我现在要做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越阶层。但是能不能成功我并不确定,或许需要10年,或者20年,或者是永远。可是我坚持是自己的选择,我知道学习的知识只是基础,社会才是真正的学校,不平等才是真实。所以我每天晚上看书学习,写作业,都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获得认知,让自己可以拥有应对未来的能力,看懂未来的趋势,让自己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
Tina:高考的时候,我和第一志愿只差三分,交钱可以上第一志愿,可以留在自己的家乡,一个省会城市,和从小到大的朋友们在一起。不交钱就要去一个比较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城市。 当时,爸妈和其他的亲戚朋友都让我交钱留下来。我也知道这里我很喜欢,钱也不是太多钱。但没有其他人知道,我的考量因素里还有一段感情。 那时候我刚知道我的初恋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了,我知道如果留下来很可能这个朋友圈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段情商可能需要很久治愈。 于是我决定去别的城市,好好度过一段可以埋头读书,学习和自己相处的时光。 就这样我在那段时间看了很多事,为很多今后的思考和学习能力打下了基础。曾经有段时间,我认为那段什么都没发生的四年就是我自己觉得的高光时刻。 再过了几年,我又重新思考:如果那四年待在家乡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我想说的是,事情最终发生的时候你只能做一种选择,之后你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也可能会一直改变,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角度会发生变化。我感觉只有以当下自己的境况做出独立判断的时候,我才会为未来因为此带来的各种后果有承担责任的意愿。否则,我就不会“甘心”会“外怪”会平白内耗自己的很多精力。
罗曼:士兵施密特为自己的独立判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医生卢卡斯为自己的独立判断成天担惊受怕,一个人从人的基本善恶价值观出发,忠于自己,与一种高度集权和机械的体制做着微小的抗衡,这也是萨特所说的自由,只是“freedom is not free.”
由此想到在武汉疫情初期被训诫的吹哨人在亲友群转的“吹哨”信息的源头提供者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大夫,今天看到对她的专访,很震动,早在12月30日她就已经报告并向医院同事发出了SARS冠状病毒的检验结果,在被医院领导以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严厉申饬后,她一边带领全科室医护人员全力以赴抢救病患,一边顶住上级粉饰太平的压力,严格要求同事们做好防护保护自己。艾芬大夫很幸运,直到目前,一直在疫情第一线的她没有被感染,作为一个医生的基本良知和专业精神支持她顶住了双重的重压。她就是一个真实、忠于自己的人。
由此又想到,有水平引用康德的名言为自己开脱的将军艾希曼,和普通士兵施密特、集中营医生卢卡斯为何对于显而易见的对错却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判断?身居高位的艾希曼难道还不如施密特和卢卡斯,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吗?尽管阿伦特“平庸的恶”这个概念真的显得很深刻挺迷人,但是我总觉得,人内心并非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而是在利益驱使或危险威胁下自己选择和相信哪一种判断是对的,至于主动或是被动,多半是个借口和姿态。艾希曼的冷酷虚伪,为什么不能解释为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选择呢?作为纳粹高官,他不一定像底层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一样会直接参与或现场目睹抓捕、杀害犹太人,他不用每天直面杀戮的内心折磨,犹太人对他来说,并不是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异类和数字,而消灭犹太人的任务执行得好对他来说也许还有利于升迁。这不正是对他个人而言利益攸关的思考、判断和选择吗?至于那些自我辩护,我认为不过是在为减轻罪行找到所谓迫不得已的借口。而施密特和卢卡斯,他们的利益攸关在于,作为具体执行者或参与者直面杀戮的内心折磨已经远远大于“忠于职守”的正当性解释所能带来的慰藉,他们的判断和选择也是基于此作出的。
我认为,在理性人的前提假设下,人的思考和判断,其实是利益攸关的结果。最近刚好又再回顾万老师第二季里介绍的塔勒布的《利益攸关》,那些看似非常荒谬的判断,就像训斥艾芬大夫的医院领导、对吹哨人作出训诫处理的领导和艾希曼,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利益攸关立场上作出的思考和判断,而无需面对或没有料到自己有一天会必须面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他们不在一线、没有利益攸关,所以倾向于依据抽象的规则判断和行事;而艾芬、施密特和卢卡斯,他们就在一线,每时每刻面对最直接的后果,承受对人性底线的拷问,他们是利益攸关的,倾向于按照真实的所见判断和行事。
贝达人:我曾经一个人反对整个办公室的“不劳而获”的作风,那段时间的孤独和自己的怪异一度让我得焦虑症。幸好我坚强地跟随我内心的声音,换了一个我自己想去的岗位,然后继续平凡但是身心合一简单地生活着。
林特特:听完这节课,想把《窃听风暴》翻出来看看。其实从没有判断到有判断,从迷失迷茫到清晰到义无反顾地坚持、执行自身的判断,也是文学作品的母题啊。
佘天俊:“满嘴都是套话,让自己陷落在陈词滥调之中,又把这些陈词滥调当成自己的盾牌和武器,用它们来抵挡现实,拒绝真正的思考和对话。” 有不少“能言善辩”的人,都是这种情况,不管你在说什么,他们都能继续说下去,不管是反驳也好,同意也好,其实也不管你说的是什么也好,他们都能接着说,但不管他们说多少,给人的感觉是一片空白。阿伦特说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他们会说,但没有思考能力。 思考能力,是积极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这里面没有套话和陈词滥调,是自己的是非对错的判断。虽然道德,思想,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如果你不把自己的判断,放在你说的话的背后,那种就是陈词滥调,的确也不应该说出来。 独立不等于正确,但等于统一。独立的价值,不是正确,而是让自我统一。 每一个价值判断,背后都有更底层的逻辑,如果不经过独立思考,而只是把各种“正确”的结论,拿来使用,就会处于一堆自相矛盾的“正确”之中,因为“正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需要独立思考,先统一标准。统一的标准比更多的“正确”重要。 当然,独立判断所面临的风险也由此而来,你的统一标准,必定会和现存的某些“正确”冲突。给自己标准,给自己立法,当然也得承担代价。自我内心的代价,社会标准的代价。
李炜:我的高中是一所典型的实施应试教育的“县中”。高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建议信,给年级组长、班主任老师和科任老师们,请他们考虑当前课堂氛围不活跃、效率比较低的情况,适当允许学生自主决定学习计划以及是否需要上课并定期反馈。年级组长(也是语文老师)拿到这封建议信后,以带嘲讽的口气在全班面前朗读建议信并否决了其中的内容。课后他把信退给了我。这可能是我高中期间最受伤的一次事情。到现在回想,已经过去12年了,当时的我在大的应试氛围中坚持独立思考,挺可贵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