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韦伯I:为什么说“祛魅”是人类的“梦醒时分”?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正式进入马克斯·韦伯的思想。
上一讲说到,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因为他完成了两件事情:看清现代和反思现代。看清现代,就是看到现代社会纷繁表象之下的本质性特征;反思现代,就是指出现代性深层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韦伯思想的具体内容,去了解韦伯所发现的这些“本质性特征”和“深层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会用四节课来讲解韦伯关于现代性的三个命题和一个重要概念。这些命题和概念环环相扣,你听完这四讲,可以再连起来,感受一下韦伯的思想力量。
“祛魅”是什么意思?
今天讲的第一个命题,也是韦伯被人引用最多的一个术语,叫做“ 世界的祛魅 ”(德语Entzauberung,英语disenchantment),也有人翻译成“除魅”。
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世界被祛除了神秘性、魅惑性”,这说的是 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换句话说, 以前人对自然的认识中有一种神秘性,后来被去除了。 那这种神秘性开始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很好理解,你想想那些生活在前现代社会的古人,你会发现,无论在哪个文明中,古人都相信有各种神仙、鬼怪、精灵。不只是人有灵魂,动物也有灵性,石头草木也有灵,万物都有灵。古希腊的那些神灵你肯定听说过。中国也有各种神仙,在道教里面,最高规格的普天大醮仪式中,会恭请3600位神仙;日本的神道教说,有“八百万神灵”;印度教说,有3300万个神灵。其实这些也不是确切的数量,就是想说世界一切现象的背后都有神灵。
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迷信吗?前现代社会的人,蒙昧嘛。对,但是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到处都是神灵的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意义非常重大, 这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 。而且甚至是可以沟通,可以互动的。漫天神灵,就意味着到处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渔船出海,祭奠一下妈祖;打仗出征,到神庙去占卜一下;生不出孩子,去求送子观音。虽然未必有用,但至少有路可走,心里是安稳的。
这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和整个宇宙紧密连接为一个整体,构成所谓的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从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人类是“嵌入”在整个宇宙之中。
那么,祛魅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用理性的力量驱散了神秘的魅惑。
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就是把祛魅当成了世俗化,人们不信宗教,就是祛魅了。其实真实的历史要比这复杂一点。我们中国人习惯把“宗教”和“迷信”连在一起说,“宗教迷信”。但在西方历史上,宗教和迷信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对应到祛魅这件事情上,祛魅其实分了两步,先针对迷信,再针对宗教。
“两步走”的祛魅
祛魅的第一个阶段叫“ 宗教的理性化 ”,就是驱逐原始宗教中的各种巫术,用哲学理性来论证宗教的合理性,论证它的救赎意义。就好像中国人也会区分江湖迷信和真正的佛法高僧,祛魅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去除那些装神弄鬼的事情,让宗教走到理性思辨的道路上来。 在这个阶段,祛魅并没有瓦解宗教,反而使宗教获得了理性化的发展。
说到这儿,你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科学家都是虔诚的教徒。比如牛顿,再比如发现了遗传定律的孟德尔,他本身就是一个神父。还有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那些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等,他们的科学素养都很高,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他们都重视理性,追求理性的发展。
但是祛魅作为一种理性化的取向,要拷问的是所有的超验、所有神秘的东西,这个逻辑链条一旦展开,是不会停下来的。 所以祛魅的第二阶段很快就转向了宗教本身。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是理性化活动最典型的体现,依靠的是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科学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的, 它在根本上抵制一切神秘和超验的事物 。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最后还是会挑战宗教的精神主导地位。到尼采喊出来“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挑战就基本完成了。
好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了。
日食,就是一个天体现象,既不是什么皇帝失德、上天示警,也不是什么天狗食日;
水,就是H20这种分子,世界上没有什么圣水神水;
你爱上一个人,不是什么前世因果,而是你体内荷尔蒙的变化。
自然世界被客观化了,不再具有神性和灵性了,成为可以用冷冰冰的因果规律解释的物理世界了。那么,这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失去默认选项会怎么样?
其实答案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 古代社会中那种无处不在的意义消失了,那些与世界的联系和沟通也没有了。 一对夫妇怀不上孩子,到医院一检查,说他们不孕不育,目前没有医疗手段,到观音庙去烧香也没用。是不是很绝望?一个人要去危险地带工作,他知道求神拜佛没有用,最多也就是给自己买个保险,真要出事还是会出事。是不是会很残忍呢?
还不仅如此。韦伯看到的问题更加深入。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韦伯所说的“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当然包括宗教信仰。但要注意, 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 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需要解释的,而到了现代,信仰宗教是需要解释的,反倒是不信宗教无需解释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了。
失去了默认选项,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还记得我前面用的那个词吗,嵌入。在古代社会,人是“ 嵌入 ”在这个世界里的,是和世界连为一体的。而到了现代社会,人被从那个大的“母体”中剥离出来,从此孤独地、无依无靠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什么意思呢?我打个比方,你就能深切地理解这个感觉。
比如一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圣诞节,等着圣诞老人给他送礼物。但是,他被告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圣诞老人,圣诞夜也不会有人从烟囱里下来,也不会在孩子的袜子里塞什么礼物。如果你收到了礼物,那是爸爸妈妈买的。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个瞬间会不会让他觉得非常非常失望?这个孩子本来和那么广大的世界相联系,是不是就被切断了?
圣诞老人从北极来,从古老的传统来,时间和空间上的这种无穷性,瞬间就消失了。小孩不再是一个无尽时空的参与者,他只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个普通小孩。对于他来说,这个节日的意义,是不是立刻就显得失色了不少?你看,他被从那个“母体”中剥离出来了。
即使你不信仰宗教,在这个例子中,你也能感受到祛魅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影响。这个孩子的感受,就是祛魅完成的过程中,整个人类遭遇的情况。
不愉快的真相
我还要提醒你一点: 韦伯揭示的“世界的祛魅”,不带有好坏价值判断的色彩,这只是一个对客观事实的描述。
一方面,他知道,这个祛魅的“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会让人茫然若失。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理性主义的科学又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
另一方面,韦伯也知道,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的真相,你高兴也好,失落也罢,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 现代性的境况 。
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世界被充分理性化,也就被人看透而不再神秘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
实际上,韦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指出了祛魅的事实。第二件事,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梦醒了,然后呢?
科学能让人从古代的魅惑中清醒,但是清醒之后的现代人怎么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呢?祛魅的世界怎么才能不成为冰冷荒凉的世界呢? 这一次,科学和理性能帮我们做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韦伯的第二个命题了。下一讲,我们继续。
问答
最后留一个思考题: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经历过上面说的那种“梦醒时分”?你觉得那个时刻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呢?想听听你的故事。
编辑按:01-04讲的小加餐,刘擎老师已经发布在知识城邦。
第一次小加餐,刘老师和大家打了个招呼,谈到了这门“思想课”的不同的“实用价值”。
具体内容,→戳这里观看。
划重点
1、祛魅的字面意思是“世界被祛除了魅惑性、神秘性”。这种“神秘”的背后,是一种“人与世界紧密相连”的认知。祛魅,就是用理性的力量驱散了这种神秘感和这种对于世界的认知。
2、祛魅有两步,第一步是宗教的理性化,在这个阶段,祛魅使宗教获得了理性化的发展。但到了第二步,理性化就进一步地颠覆了宗教的精神主导地位。
3、在韦伯的思想中,“祛魅”不是一件好事或者坏事,它只是一个我们需要直面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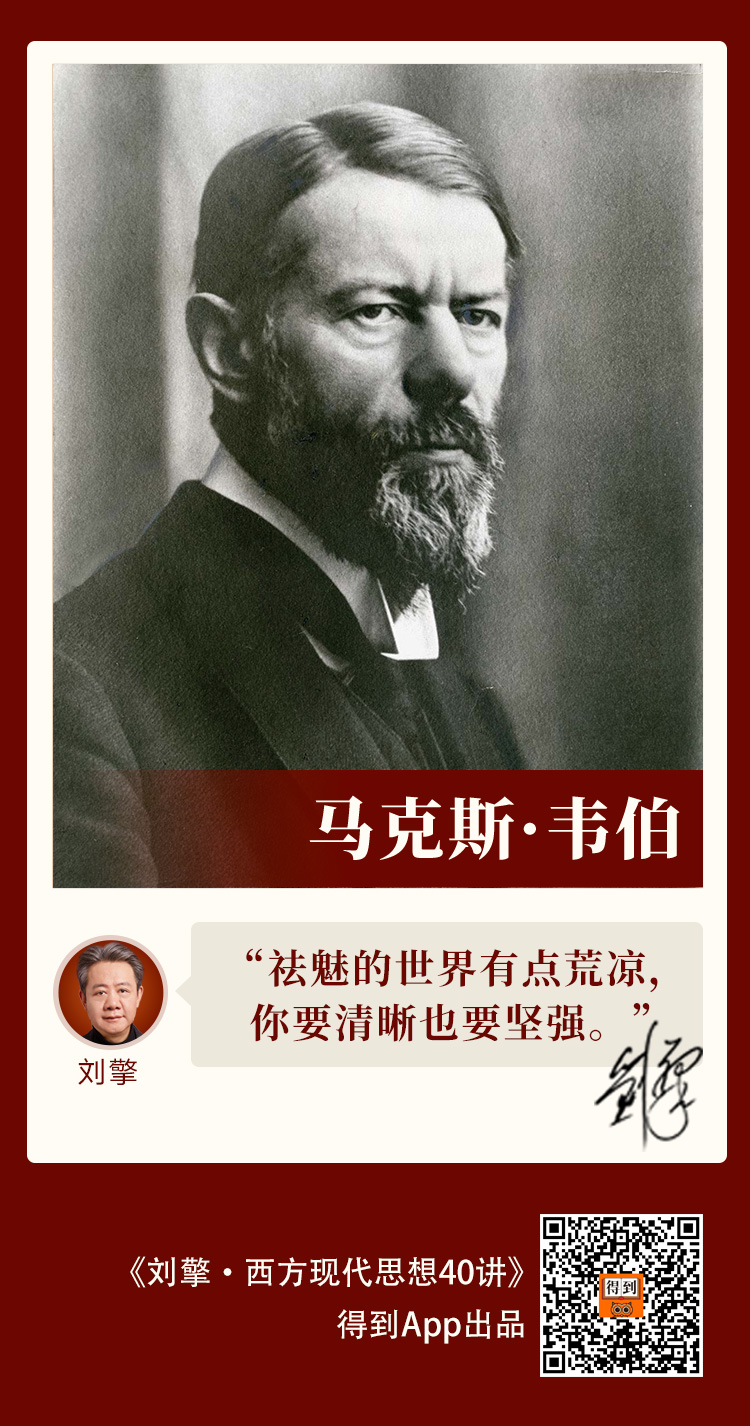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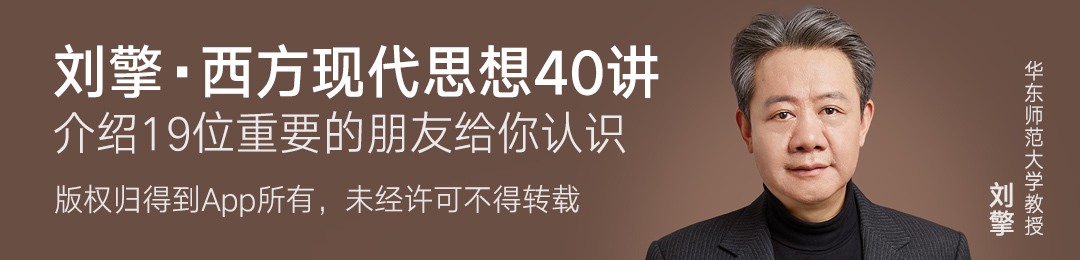
热门留言
nick:虽然称不上是“梦醒时分”,但我智识生活中所受到的一个重要冲击恰恰是来自于阅读韦伯的《学术作为志业》本身。 不得不说,韦伯给他这个演讲起了一个对我(甚至可能很多人)极赋诱惑的题目,让我(们)以为能从韦伯的教导中寻到纵身跃入科学的意义,但读完之后才发现韦伯给的是一个当头棒喝:科学不再提供意义了。甚至科学不断在蚕食意义那逼仄的空间。那科学本身还可以被“信仰”吗?科学还是一种志业或天职吗? 我想起柏拉图的洞穴之喻,那个走出洞穴的人,当他进入韦伯的时代之后,他是否会感到洞穴外真实世界的乏味无趣,而怀念洞穴里墙壁上那美好的皮影戏?也许人其实到头来还是需要洞穴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智识经历对我是好是坏,但是如果科学家告诉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承诺不过是苯基乙胺副作用的结果,那我可能会选择老老实实待在洞穴里。
邹经纬:晚餐时和八岁的孩子一起听的,老师一说到圣诞老人的礼物都是爸爸妈妈买的。。。孩子的表情顿时就变了😅
刘擎(作者) 回复:实在抱歉,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给孩子“剧透”了。
伪装: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经历过上面说的那种“梦醒时分”?你觉得那个时刻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呢?
在得到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说我在不断的经历“梦醒时分”,从各种搞不清就归因于某个神秘的存在的嵌入感中被拉出来,就好像大冬天没穿衣服现在了冰天雪地里,瑟瑟发抖也抖不出身体需要的热量,感觉糟透了。 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的责任和负担,也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这种“梦醒时分”虽然初期打击很大,但是习惯以后就有种通透的感觉,利大于弊。 唯一的麻烦就是知道的越多越孤独,也就越是想要找到同路人,幸好得到这个平台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治玉:如何理解世界的驱魅呢?人们都是在一片迷茫中,迎来了理性主义,把人们从黑暗中带了出来,在我们坚定跟着理性主义走的时候,我们很是迷茫,因为我们和世界剥离了,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前不曾看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理性和概率控制的。就好比一个原始人,一下子来到了电子世界,看到了神迹,接着就给他展示了神迹背后的现实。不管是相信神迹还是相信现实,都是可以的,就是害怕这个原始人,在知道了神迹以后,还要自己欺骗自己,不愿意面对现实这个真实世界。 韦伯就是那里带着我们认清眼下的一个智者,社会的发展不是设计好的,是人们在不断地摸索中,误打误撞所形成了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而合理不是正确的。如何理解合理的世界,是每个人的必修课。这就是说明,我们在理性面前无比自信又无比的渺小。 世界的祛魅就是一个韦伯给我们展现的现实,现实如此,就是如此。以往我们依靠宗教信仰,现在我们需要依靠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了。不是选择少了,而是多了一个选择。 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共同的信仰或者说共同的价值观不容易统一了。
刘擎(作者) 回复:您说得特别好。“存在即合理”这句话现在也是被误用得挺多的,点出“合理”不等于“正确”这个意思也许很重要。“多了一个选择”也说得特别在理。(来自编辑)
金戈铁马:开普勒是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者。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作科学研究时,他回答说:“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分享神创造世界时的快乐。”他还曾说过:“我单单只信耶稣基督的工作,在他里面有护庇和安慰。”事实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比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等。这源自于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对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重要影响,也证明了宗教与科学、理性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作为基督教徒,他们坚信上帝和造物主的存在,宗教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寄托;而作为宇宙学家,他们是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和理解上帝是如何设计宇宙的种种奥秘的。正是由于基督宗教的信仰,让这些宇宙学家们拥有了坚定的信念,他们认为神学对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种种解释是不正确的,这让他们能够坚持不懈的去探索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的;而通过科学的方法,运用数学的工具去解释、验证宇宙中的种种现象,又让宇宙学家们不断接近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依然要荣耀上帝,但只是让上帝仅仅具备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而再非万能的造物主。所以,在宗教信念的支持下,反而推动了现代科学和理性思想的不断发展,也诞生了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这可以说也是世界的一大奇妙之处。
用户11191885:刘老师您好,针对您举的圣诞老人传说破灭的问题,我想提的问题是,尽管像圣诞这种宗教信仰的丧失可能会让人感到与传统和广大的世界失去了连接感。但世俗世界由于理性化的构成,他可以了解历史和其他众多民族的风俗,甚至去亲身体验全世界,这种多样性,深度和更加自由选择的丰富体验难道不比幻想式的,单调无法触及的信仰更有吸引力吗么?进一步说,如果所有信仰和精神需求都可以还原成体验,那么,追求最大化良好体验的体验主义,是不是有成为理性化时代信仰的可能呢?
刘擎(作者) 回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所表达的想法,许多世俗化的理性主义者都会赞同。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告别了传统的或者超验宗教的信仰,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这种立场有一定的依据,也可以得到某种论证(justified)。 但这种论证未必能说服传统主义者或宗教保守派。他们反驳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点就是针对你所说的“体验”。 在他们看来,从理性主导的观察和观察中所获得的体验完全无法取代传统的或者宗教性的体验,这两种体验的感受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世俗主义的体验是从观察者、鉴赏者的外部视角开始的,通过理性的认知和理解才能逐渐深入,一旦遇到理性认知无法把握的感受模式,就会无法深入其内部。 而传统或宗教的信仰也可能诉诸理性,但不依赖理性,能够让人获得“沉浸式的”更为内在的体验,这是理性主导的感受模式无法抵达的。 我自己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反驳。 然后,你在“进一步说”之后的描述可能更有问题:“所有信仰和精神需求都可以还原成体验”,在这里“还原”是什么意思呢?能够还原为同一种类型的体验吗?参观教堂的“体验”与在教堂中信徒做弥撒的“体验”是相同的吗?彼此是可以比较、可以“公度”(commeasurable)的吗?如果彼此无法公度,你就无法从中得到一个“最大化的良好体验”。 在宗教保守主义者看来,世俗主义者预先否定了超验存在和神秘启示,就无法抵达信仰的最深处,必定会有所损失。而世俗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这仍然是争议不断的难题。
李亮:老师好,请问祛魅的德文是什么?以及英文翻译怎么写。感觉中译有点难理解。
刘擎(作者) 回复:德语是Entzauberung(有学者考察认为,这是韦伯援用诗人席勒的一个术语);英文最常见的译法是disenchantment。中文有许多译法:除魅、祛魅、除魔等等
Vinchent:其实学习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祛魅”的过程,我印象很深的是,以前电脑出问题的时候我只会重启,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找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干过在电脑司机的时候拍拍机箱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学了计算机之后,我就知道了,电脑死机一定是有原因的,而如何去查找原因是有迹可循的,最起码,我能够判断哪些问题是我重启就好了的,而哪些不行。
我不能说我们的物理世界和电子机械世界一样,但是科学的研究就是为我们理解种种现象提供一个抓手,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说,人类“学习”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自我祛魅。从简单的迷信到科学化的宗教,这也是祛魅的过程。
说回到计算机,在有些我不掌握的领域,我还是会觉得有些现象很神奇。程序员界有一句话叫“It works on my machine”这可能也是程序员的终极谜团吧哈哈。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祛魅不止。
不过我的疑问是祛魅究竟是现代化目的,还只是一个结果而已呢?这个结果除了让我们更加博学,为我们带来了高于迷信和宗教的价值了吗?
Sencer:今日思考,听着今天的课有一种润物无声之感,好像为自己的空虚找到了答案。今天的我们虽然没有了过去人的迷信,但是却会就被各种各样的权威笼罩,父母、老师、学校、领导、单位,在我们眼中他们好似无所不能,有着像神一样的地位。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逐渐老去,老师或许也成了同事,学校成了永远的回忆,领导有的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成为了阶下囚,又或者会成为自己的同僚或者是下级,单位也有可能消失。原来像神一样崇拜瞬间变得虚无,有时候甚至会怀疑一切,可是这一切都会继续循环发生,当自己离开今天的岗位,原来在岗位上的一切殊荣也不复存在。 也可以说那些幻觉的坍塌给自己带来的是更多的反思,反思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是为了挣永远也赚不够的钱?买更大的房子,获得更高的权力,享受更多的极品。事实证明,这些事物都不能足以让一个人感到富足,甚至还会因此惴惴不安。也可能是自己没有达到那一个高度,不能明白那种身居高处不胜寒的凄凉。 那些空虚曾让我不知所措,以至于让自己不愿意去面对那些所谓的现实。随着学习与思考的深入,我逐渐明白了,只有精神上的富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足,只有精神上的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那些依赖于外力给予的自由,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崩溃。想要获得真实意义上的自由,就需要用丰富的知识来滋养自己贫乏的头脑,从知识中获取力量,让自己有力量去面对事实与真相。
戚志光:祛魅是世界的真相,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就跨入了“知识的诅咒”,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中学时学习物理,老师讲到太阳终将燃烧殆尽,地球将会被吞噬,一切生物都将化为乌有。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的神经被某些东西挑动了,这个世界变得不再稳固。或许对于我来说,那一刻,是世界祛魅的开始。
天天天蓝:刘擎老师您好! 喜欢您深厚的声音,我用1.5的倍数听音频,同时看文字,不需太集中注意力,就会被您的讲述深深代入!
梦醒时分是什么时候?梦醒之后,又该怎么做? 韦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指出了祛魅的事实。第二件事,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梦醒了,然后呢?
客观事实的描述是不会变的,人心从有魅到祛魅这个过程,足以改变人的行为,人类史也一直是一个祛魅史,不是吗?客观事实没有七情六欲,而人天生具有七情六欲的,我们天生会对没有七情六欲的客观事实产生七情六欲,这,就是梦醒后,看清事实,认真喜恶。
小孩子发现圣诞礼物是爸妈买来的,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但他的能力不足以证伪,他可以一直的存在质疑,但仍然心怀梦想。这份美好的期待,会在长大后,用自己买的圣诞礼物送给孩子得到了证伪,但这份真实的礼物陪伴他许多年,这份美好让他愿意给自己孩子一个美丽的梦,这就是他祛魅的过程。梦醒了,他让美好的梦继续存在记忆中。
我睁着眼睛想,“我”看到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吧,如果没有镜子,“我”的世界为什么没有我?偶尔抽离的看待自己,“一个人”在睡觉、吃饭、学习和工作,她不悲不喜,只是一团物质,而思想,已穿越时间、穿越时空,或喜或忧。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我的梦境。梦醒了,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客观世界的自己。
很期待您接下来讲韦伯的“梦醒了,以后怎么办”
佘天俊:【“世界的祛魅”,以前人对自然的认识中有一种神秘性,后来被去除了。】 【神秘性,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人是嵌入在宇宙之中,连接为一个整体,构成所谓的宇宙秩序。祛魅,意味着,用理性的力量驱散了神秘的魅惑,人被从宇宙母体中剥离了。】 【祛魅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不再有神秘性作为人类共同的默认选项。】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以前的神秘性,理解为一种全人类共同的“法律”。所有人共同遵守,但不需要证明,不需要证明每一条遵守的“法律”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确,只是存在并遵守。而理性化的祛魅,让人有了自行验证的能力,也让了有了自行验证的冲动,个人就不再满足于接受原本不需要解释的“法律”。 失去了超越人类的最终裁决,寻找证明,成了每一个人无休止的,没有统一标准的事情。
magarita:我爷爷家住在六楼,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放学回去,爷爷总会在我开门前一刻有预感我要敲门一样,把门打开。后来次数多了,在不一样的时间回去,他也还是如此,我就问他怎么这么灵光,他笑眯眯地对懵懂的我说因为有心灵感应,我们是爷爷和孙女啊。我当时还真的觉得这是一种血肉亲情而带来的一种超能力,哈哈。多年以后,在他老人家早已仙逝的一年餐桌上,和奶奶偶然聊起这件事,奶奶不无感慨地告诉我,那是你爷爷耳朵好,你上楼的脚步声和别人的不一样,他一听就能分辨出来,所以才这么“神”。怎么说呢,虽然得知真相的我有点不甘,因为爷爷在我心里的光环少了一点,大概也是老师您上面提到的自然的神秘被驱散了一点,那种生命中被联系的感觉消解了一点;不过,这真相也不算完全是梦碎时刻,我爷爷以前是铁匠,常年的劳作让他的耳朵有所受损,就是这样,他仍能认出我上楼的习惯,不知是我小时候的脚步太过活泼明显还是爷爷特别关注我这个小孙女了。后来回奶奶家,上楼每每思及此处,我还是很受感动,这份心意值得我长久珍惜。
老马识途:去魅之前,人类普遍认为世界是由某种神秘力量主宰,有一套普遍运行的规律,人只是被动的参与到运行当中,没有自由,人的创造能动性微乎极微。去魅后,是科学理性把人类从“旧剧本秩序的故事里”拉扯回到多元认知的物质世界。抛弃虚无回到真实,人从被动的演出转变成了主动改造。原来被压抑的自由、创新是人的欲望和天性,被释放出来后,人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失去了普遍标准,变得多样复杂了。人类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标准。这也是导致人类社会现代矛盾的根源。
郝景宇:刘擎老师好,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在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在于人类拥有想象力,想象力促使人类更好的实现群体合作,克服个体劣势,进而一步步发展出社会。在我看来,祛魅的“梦醒时分”是将千年来人类社会集体想象所公认的价值体系(信仰)解构了,因而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而理性化的建构过程却不以对“人生的幸福”作为的重构目的,正如上一讲所言科学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 但无论我们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和失落,都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现代性的境况。当然你尽可以选择继续装睡,相信某种被宣称为真理的造梦功能,只要你能承受得起装睡的代价。想到这我忽然想起有句话说自由,是强者的选择。
Elaine:胡適最早在中國呼應西方思想,說出「我不要孩子,孩子自己來了。」孝道倫理於是逐漸被檢視,被評斷,從「不需解釋為什麼該孝順」,到需要教育「為什麼要孝順」,我們打掉了原始的洞穴,才發現無處可避風雨。但是遮風避雨是物質上的需要,也是心理上的必須。待在洞穴裡是安逸,走出洞穴是驗證自己的心智。尼采說「上帝死了」,不是笑著說的。他是告訴大家,「好日子沒有了。」— 但不代表我們就一定要做一個悲劇性的流浪漢。
本熊熊:小的时候看卡通片、动漫或者是语文书上的插画,我都感觉自己可以进入那个世界,那里真的好自由啊,各种有趣的动物伙伴和温暖热血的故事,太畅快了…但是长大的我已经很难进入这个世界,这种不可逆的变化好失落。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玩的尽兴,好好享受童真的世界
术子米德(吴惠敏):从小学数学,考数学,一直拿高分,觉得脑子灵 某日去图书馆,服务台询问数学在哪里,被答复我们这里没有课本,新华书店有数学书 某日在得到学习课程,得知数学不是科学,它是在人类思维体系下,公理化的演绎系统,又得知当代物理学就是基于数学,无数学就无当代物理学 那种震惊,现在还没有消退,至今还无法完全理解,一门人类思维构建的公理化演绎体系,支撑着当代科学里最辉煌的物理学这顶皇冠,难以置信的震惊。
曾凯:有过这种时候。我过去的人生故事一直是: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我一直在寻求突破父母的禁锢,无奈父母一直在压迫我,不允许我离开他们的世界。 直到去年在得到学习半年之后,某次和父亲喝酒时候他说其实他一直在支持着我,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兑现过自己发出的一切愿望。 从这件事里,我终于发觉原来从来没有为自己负责过,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父母身上。 这个世界从没有认真的反对过我,而是我自己从没有认真的面对着这个世界。 从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一切的发愿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的。 我想这也是我自己人生里的祛魅。
成洁getit:正式上班第一年,向带我的师傅求助了一件事,他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具体的细节忘了,当时觉得醍醐灌顶:我也是有职业责任要负的社会了。 因为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观察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调用“他者”的视角,我曾经揣测他们是不是会有更好的心理调节体系、更少的心理问题,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精神依靠,而无神论者会有面对整个世界的无助和渺小感。皈依和依靠、自由和自立,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梦里没有理性,梦醒有理性却也直面更多压力。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