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韦伯II:现代的“诸神之争”是怎么发生的?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上一讲我们讲了韦伯的第一个重要命题,“祛魅”。这个词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有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过去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宇宙的整体秩序。现代的科学理性驱散了这种神秘的气氛: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理性去认识世界。科学理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
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韦伯的第二个重要命题: 诸神之争 。注意,这里的“诸神”并不是指多种神灵,而是指人们各自信奉的价值观,诸神之争就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现在信奉某种价值观,就有一点像古人信奉神;观念的冲突,就像是神灵之间的战争。
科学理性是价值观战争的胜利者吗?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刚才说,科学理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如果说有一场观念的战争,那么科学理性不是已经获胜了吗?
没有这么简单。这是一场终极价值的战争,科学理性并没有获胜,实际上,“价值之争”根本不是它的战场。用学术语言来说, 科学理性发挥自己的作用有一个范围,它不能为人类生活的终极价值提供答案。 科学理性发挥自己的力量,是在事实判断的领域,而“诸神之争”的战场在这个领域之外。
什么叫 事实判断 (fact judgement),就是 你做的判断是在描述一个事实 。比方说,“清华大学在北京”。这就是一个事实判断,清楚明白,只要到清华大学看一眼就能验证。 事实判断是在回答这样一类问题:一个事物“实际上”是什么。
但在生活中,我们还会做出另一种判断。要是我说,“清华大学应该搬到上海”, 这就不是在说“实际”了,而是在说“应当”怎么样。这叫做“ 价值判断 ” (value judgement) 。 在这种说法里,隐含着一种价值高低的取向。说“应当搬到上海”,其实是在说“在上海会更好”。不过,大部分北京人都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
价值判断的问题就在这里。对事实判断,我们很容易达成一致,客观现实摆在那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价值判断不一样,我说上海更好,你说北京更好,我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很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逻辑上, 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一个鸿沟:它们的判断标准不一样。
事实判断,有一套客观标准去验证它。梨子甜不甜,吃一口就知道;清华大学在哪里,去一次就知道。在这个领域里,科学理性是无敌的高手。
现代科学发展了几百年,有一套成熟的事实检验手段。有科学仪器、有实验方法、有学术审核机制。只要是说事实,就可以回到现实中去检验。比如“黑洞”,最初是物理学家提出的一个理论预测。但它是在预测一个物理现象。那么我们去测量各种数据、去给5500万光年外的黑洞拍照片,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事实问题总能搞清楚。你看, 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
价值判断就不一样了。价值判断是要分辨好坏对错、高低优劣。这也需要一套标准。在古代,我们相信世界有一个统一秩序,即使这个秩序一般人说不明白,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观念,就是终极答案是存在的。然而在世界“祛魅”之后,我们知道了自然世界就是物质的, 物质世界没有什么神秘的终极答案。
现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 这套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受到各种个人因素的影响:国籍、文化、性别,甚至职业、家境、爱好都会影响到个人的价值标准。比如说,如果你家有一只养了十几年的宠物,不管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原因养的,到现在,你和完全不养宠物的人相比,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倾向。 在价值领域,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
事实判断有确定性,是因为它有章可循,这个“章”就是公认的判断标准——客观世界。而价值判断,相对来说无章可循,或者说没有一个公认的“章”,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的答案没有了,留给我们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选项。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
价值多元化麻烦在哪里?
平时说起“多元化”,一般是正面表扬,这里为什么说多元化是一个“困境”呢?
当然,多元化有好处: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举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你不信教,可能会很危险;但现在你可以自由选择相信或是不信。这就是多元化积极的一面。但是,价值多元化也有消极的一面。
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
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有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之前课程里说,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
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 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的对不对。 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这造成了一种“ 价值真空 ”,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这是个人精神层面的问题。
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
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上都是 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比如,美国政治辩论中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堕胎的合法化。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但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所当然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你看,这两种观点背后都有它的道德依据,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冲突很难用理性来化解,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哪个道德依据一定“更正确”。
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比如,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秩序;如果是后者,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美国政坛,这个话题争吵了几百年,目前看来,不仅没有“真理越辩越明”,反而是政治分裂和派系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歧呢?韦伯给出的回答有些冷酷,他说: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如此的深刻,以致于许多冲突无法化解。终极态度彼此互不相容,它们之间的争斗也不会有结论。
这里我要留一个小伏笔。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像韦伯说的那么绝对呢?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同样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之后会具体讲到他的思想。
难以终结的“诸神之争”
现在还是回到韦伯,回到诸神之争。 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到了价值领域,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不断冲突,这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
但科学理性给现代社会还带来了别的麻烦,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问答
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价值观念冲突的问题呢?对于这种问题,你是怎么看待、怎么处理的呢?欢迎到评论区留言,表达你的见解。
编辑按:01-04讲的小加餐,刘擎老师已经发布在知识城邦。
第一次小加餐,刘老师和大家打了个招呼,谈到了这门“思想课”的不同的“实用价值”。
具体内容,→戳这里观看。
划重点
1、韦伯说的诸神之争,指的是价值观念的冲突。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现在信奉某种价值观,就有一点像古人信奉神;观念的冲突,就像是神灵之间的战争。
2、有两种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在表达“事物实际上是什么”,价值判断则是在表达“事物应该是怎么样”或者“事物怎么样更好”。
3、韦伯认为,在事实判断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但在价值判断领域,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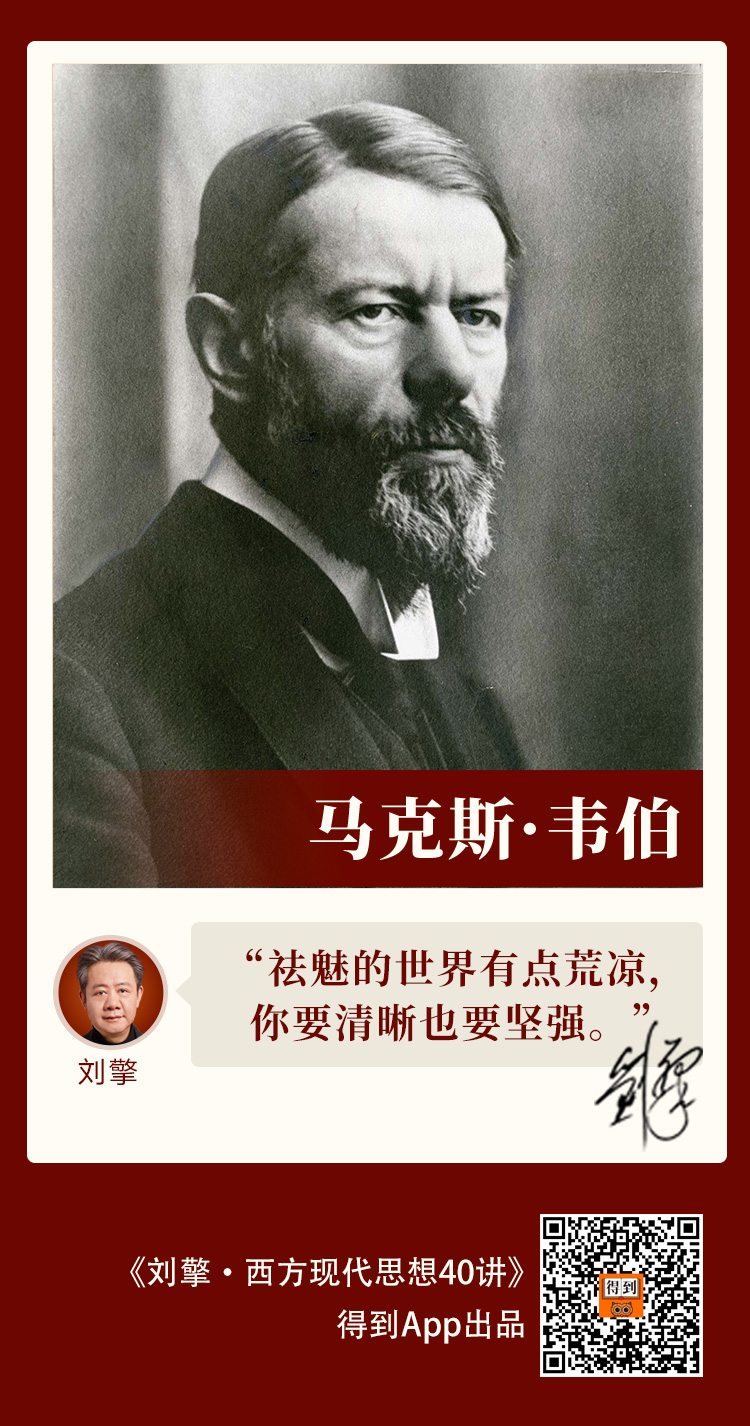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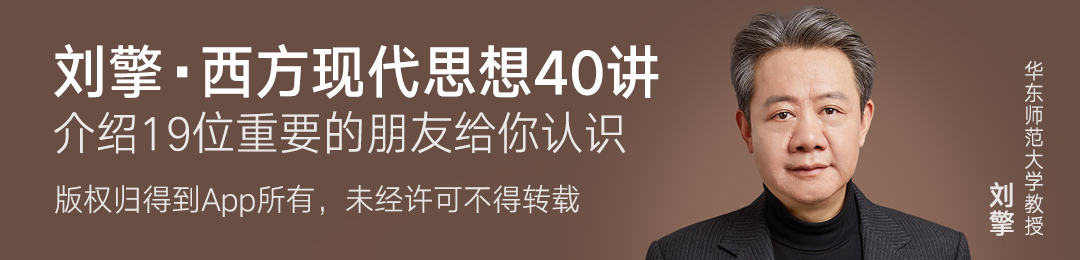
热门留言
可:请教老师,古代价值观也不存在唯一标准啊,也是不停的抗争和演变,这不是现代才面临的问题吧?差异是什么?
刘擎(作者) 回复: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政治现象始终存在。在古希腊就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苏格拉底用不着总去和人辩论。欧洲宗教战争当然也是典型的例证。但有一个重要的古今差别:在古代,大多数人相信,统一标准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信奉一个标准答案,而且这个答案也是可以找到的。那么价值分歧和冲突就是一种不正常、不可接受的状态,是需要克服的。但现代人就不一样了,我们开始怀疑甚至不相信存在统一的价值标准,更不用说能够获得了这个标准了。于是,多元价值的状态不再是“异常”,而是成为一个“新常态”,不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作为人类的处境被接受下来了。所以,现代的人们经常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这很正常”。
佛祖门徒:“我们生命里的重大决定,并不仅仅关乎于你想做什么,也关乎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句话道出了价值观对于人生重大决策的选择基点。 当面临卖掉公司变现和继续苦逼创业进行选择时,合伙人以退出相威胁要求选择前者;当面临应该保持业务专注还是选择多元化经营的争论时,很多人都认为应该以赚钱为首要。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三个问题,“十年后我会为当年的选择后悔吗”、“我能承受放弃的机会成本”、“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能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往往能够找到答案。
青年导演叶彤:我觉得对此类问题的教育我们国家是相当缺失的,所以我从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教给她,世界上有两种问题,一种是1+1这种有标准答案的,一种是应不应该吃狗肉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
淸风徐来: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年少时,我执着地努力过,等到上了大学,我发现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有了工作后,我认真地奋斗过,等到有了一定的成绩,我发现这种奋斗是有意义的。有了家庭后,我投入地负责过,等到有了幸福的感觉,我发现这种责任是有意义的。一番人生风雨过后,蓦然回首,我发现努力、成绩、责任以及幸福背后的那份真诚、善良与爱心才是最有意义的。
简单_透明_规范: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有句名言「同时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很多时候我们工作是为了挣钱,但兴趣+自信心才是我们工作效率,注意力,效率,创造力的和高产出源泉。 事业的发展前途当然非常重要,但一定要爱上自己的工作才有可能真正把事情做好;而爱上一个事物则需要刻意练习,因为更多时候成功才是成功的母亲,不断刻意练习用小的成功激励自己。
佘天俊:【诸神之争:价值观念的冲突】 【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在价值领域,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 【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的对不对】
在理性祛魅之前,好像是包办婚姻,而科学理性之后,变成了自由婚姻。 就像有一个调查得出结论,自由婚姻让人们多了选择权,但并没有增加幸福感。我们本以为,选择权是一种权利,但我们忘了,没有白得的权利,没有白得的多元化,所有的收益都有成本,在我们享受选择权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了为选择负责的义务。 就如同包办婚姻,人生是否幸福,在理性祛魅之前,本来并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神秘性可以解释一切的时代,只告诉你神的解释,但并不保证你幸福,也没有人问这样是不是会幸福,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当科学理性开始解释所有的一切,这样是不是会幸福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昨日雪碧:两天两夜未曾睡觉,经历了白日做梦,那种飘飘然的梦幻很招人喜欢,而内心中出现的醉生梦死四个字告诉自己,这样继续幻想下去会把自己掏空的,唯有解决眼下的每一个小问题才能走出梦幻世界,我想这应该就是老师说的祛魅吧!而得到的出现引领着我一直寻找着曾经提出的问题,给自己的生命寻找着意义!当心理,哲学,经济,政治课程的设立重塑了我的思想形态,在面对世事无常的世界,得到是我人生路上的大学堂,是贯穿我日后生活隐形线路。冲击内心世界最强的是哲学,我找到了朋友!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我很庆幸,遇到得到,并指引我走向象牙塔!
金戈铁马:其实,关于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屡见不鲜。比如巴以冲突的双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双方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有返回家园、重建犹太人国家的权利和神圣使命;巴勒斯坦人则认为有保卫家园、保卫自己人民的权利。两种价值观之下,返回家园的正义和保卫家园的正义不断发生冲突,愈演愈烈,永无休止。我也有几位以色列的合作伙伴,他们的说法并不是为了报复,而只是出于自卫;显然,对于同一件事情,大家的看法并不一样,且很难取得认同。所以,面对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很难找到整齐划一的评判标准;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去接受、并且尝试于不同的价值观共存。学会认同世界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复杂性,懂得接受批评、承受无奈和失望;或许,这才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和常态吧。
明明的胡说八道:我发现事实判断就是连小孩都可以接受,而价值判断就是小孩都可以和你争一争,更何况我们成年人呢。就像你带个孩子去商场,而孩子看到了一件他喜欢的东西,就价格来说可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呢,我们如实的和孩子说,宝贝,这礼物已经超出了妈妈的预算了,今天不能买,一般孩子通常有点舍不得但是也不会哭闹就走了。但是,如果我们说,你看这和你家里的什么什么玩具一样的或者说这有什么好玩的,再或者说这玩具不值得,那可完蛋了,孩子一定会和你没完没了的争辩。所以,我认为和大多数人做事实判断的沟通,而只有少数人我们才做价值判断的沟通,这就是得一知己足已的原因吧
三年二班:刘老师您好,我对这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分有些困惑。一方面,这似乎不是一种语言句式上的区分,比如“你可真不是人”这就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他应该挺喜欢你的”这就是一个事实判断。另一方面,这种区分在逻辑上也好像说不通,事实判断并不总是要么黑要么白,比如胚胎究竟是不是人这个命题。而价值判断虽然多元,但也不意味着一定没有某种统一性,毕竟复杂的问题不见得就是无解的问题,也不见得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所以,这两种基本判断的区分究竟有没有更深入解释呢?
刘擎(作者) 回复:你好,我是这门课的编辑。说说我的理解吧。首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分当然不是语言句式上的。二者的区分在于,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可验证的评判标准。并不是“非黑即白”就是事实判断,“复杂多解”就是价值判断,这是因果倒置了。是因为事实判断有明确的、客观的、可验证的评判标准,所以容易得出明确的答案;价值判断可能存在多种评判标准,所以复杂多解。(而不是反过来。)而价值判断之所以可能存在多种评判标准,是因为它本身是对于事物是否是“好的、优越的、有价值的、可欲的”的评判,这种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往往受到主观因素的极大影响,所以具有多元性。有兴趣的话,欢迎你继续关注后面的课程,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和伯林的多元价值论部分,还会涉及到相关的内容。
陈C:每当我们思考和讨论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应该怎样”时,我们就要意识到,我们展开的,并非基于客观事实,而是以观念预设、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分歧可能长期存在,完全的共识无法达成。回过头再看前面讲过的“理性化”,可以看到韦伯给这一进程下的就是“事实判断”。我们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在获取事实信息前就急于下价值判断,这是我们应该警惕并反思的。
当代年轻人遇到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每次回老家都会被父母,甚至“七大姑八大姨”仔细盘问,有没有对象?啥时候结婚?要娃不?且不论要不要孩子这一“后续”问题,仅仅是要不要早结婚甚至“要不要结婚”,老一代人就和年轻一代有着很深的观念鸿沟。在老一代人看来,婚姻是关系是相互扶持、相互提升的一条途径,早结婚能帮助自己成长。而在很多年轻人看来,结婚并非人生的必需品;即便结婚,也是要在打理好自己的事情之后。
我和父母间,在这个问题上就多少有一些分歧。不过总体上讲,我是基本上认同,婚姻有利于个人心智的成熟,婚后两口子相互照顾也会比单身更好,诸如此类观点的;而我的父母,在我个人的问题上是支持我自主决定,甚至会主动维护我的自由的。至于结婚的时机,我明确表示过,在事业发展等方面有了清晰的方向之前,也没有心思去谈婚论嫁。对此父母虽然也有异议,但仍然是支持我的。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分歧都是“局部”的,并非所有观念层面的对立。因此在遇到观念的冲突时,先分析清楚,观念上有何种共识,又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多大的分歧,对后续的沟通有着积极的意义。
毅思维:在这次的新肺炎的问题中我们就面对了这个问题,面对武汉“封城”,面对其它大大小小的小区封锁。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呢?目前我不知道答案
长沙熊劲松:听课两课果断下单,虽然前面定的很多还没听完。 目前是放下了其他的,等着这个更新。从卓克的科学课,听完有些疑惑进入宗教学,学了后怀着疑惑偶然听到了刘擎老师的西方思想课,好像是专门来解决疑惑的,巧了。
山里有本书:微信圈里流行一句话:“不谈三观,其乐融融。一谈三观,不共戴天”😂 可见价值观一致是多么重要。 遇到价值观冲突的时候,若是交情浅,一笑而过,交情深的,要辩驳辩驳,或被说服,或说服对方,达不成一致时,要么撇开价值观,一分为二地继续保持友情,要么就是翻脸,绝交。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微信圈里发绝交信的,当然,这绝交信不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表达的复杂情感,而是立场鲜明的。 夫妻因三观不合离婚的,也听说过。当然,这是发生在知识分子之间。😂这是科学理性尴尬的一面了
刘擎(作者) 回复:你好,我是这门课的编辑。看到你的留言,想起来刘老师在邵恒头条做过一期关于“三观不合”问题的问答,搜索“三观不合怎么办”,往下拉一拉就能看到,有兴趣也许可以看看~
三年二班:这条留言是对编辑对我的回复的回复哈。如果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客观的和可验证的标准,那就预设了道德非实在论,熊逸老师在他的课程里多次强调自己的道德非实在论立场,但或许刘擎老师会反对这种看法。我感觉我自己还没有想明白,既没有想明白事实与价值命题区分的充要条件,也没有想明白价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刘擎(作者) 回复:这当然是困难的问题,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哲学上没有定论,也就不会期待在这里能得到满意的回答。我简要澄清一下。 (1)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有区别,因为它们服从不同的逻辑,这是休谟的见解,很少有争议; (2)但两种判断依据的标准不同,并不能直接推论说价值判断就没有客观标准,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两种判断需要两种不同类型的客观标准; (3)“价值纷争”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价值没有客观性的可靠证据,因为你可以说,这种“主观看法之间的分歧”可能就是“对与错”之间的分歧,有些主观看法是错了,背离了道德真理。 (4)当然,这种反驳就需要以存在moral truth为前提,也就是采取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的立场。 (5)道德实在论成立吗?这是道德哲学中的经典难题,有人称之为“柏拉图和尼采”的争论。我自己取一个“弱版本”的道德实在论,因为我相信某些最底层的道德原则是“真实存在的”(real),来源于人类演化(也就是说,我有点相信道德演化论的主张)。比如,禁止滥杀无辜的戒律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可能就是人类演化的结果。
马宏: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观念冲突是出现在家中老人病危抢救时医院让家属签字是否送ICU抢救,一种观点认为无论病人有多大的痛苦都要进行抢救否则活着的亲人情感上受不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老人不应该在生命最后阶段承受痛苦,应该尽量减少痛苦平静的走完一生。我的父亲96岁高龄时在离世前面对过这种冲突。最后我以长子身份不顾妹妹的反对决定不做切气管等抢救措施,让父亲自然地离开这个世界。但为此妹妹一直不能接受。
佘天俊:可不可以说,过去的“权威”是客观和主观的双重权威,权威就是一切的权威。而科学理性的出现,才导致了客观和主观的分离。当然在分离刚发生的时候,人自然是不适应的。本来权威解释一切,现在却变成了客观有客观标准,主观得另找权威。或者说,原来的权威在客观领域的崩塌,同样波及主观领域,导致了全面的信任危机。 同样,在权威崩塌之后的世界中,主观上的我喜欢,变成了自己成为自己的权威,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是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情况。开始的生活,自然会对自己能否成为自己的权威,用我喜欢作为选择,是否正确,存在怀疑。 诸神之争,可能只是科学理性加入权威系统之后的,阶段性产物。当每个人愿意,和理所当然的成为自己的权威的时候,可能诸神依旧在,但不争了。
-Lynn🔆:现代人信奉的某种价值观,其实就是古代人信奉神灵。 昨天看了润总一篇文章。事实有真假,观点无对错,可以细分为四种:事实(Fact),观点(Opinion),立场(Stand),信仰(Belief)。 事实是今天30度;观点是她觉得冷,你却觉得热;立场是物业说冷,因为热就要开空调了;信仰内逻辑自洽,信仰间互相矛盾。
还没想好换个什么名字:我记得最开始读韦伯是跟一个人类学的朋友问意义的问题。人对意义的追求,实在是一种本能一样的东西,更严重的是,没有意义,人还能生存。这个意义经不住不停的问,好像是维特根斯坦说的,问题不是一直问下去,而是选择在哪里停下来相信。意义线性的问下去,无穷倒退,非常可怕。我没想太深,只有一点想法,就是可能这不是个深度问题,而是一个宽度问题,需要一堆不能独立发挥作用的棍子支撑起来一个蒙古包。
半支烟:我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科学提供的事实观点,但是是否相信科学就是一种价值观点吧? 如果不相信科学,我们是否可以说就是没有事实观点呢? 而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上帝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事实。那么他的这种相信是价值还是事实呢?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给出什么样的答案更合适呢?
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的共识,一些问题似乎就永远没有“正确”的答案。
刘擎(作者) 回复:这个“奇怪的想法”包含着几个问题,但提问的方式有些含混。是的,提出问题和澄清问题,往往需要一些知识准备,特别你想涉及深入的问题。 比如你需要澄清,你说的“相信”是什么意思呢?而“相信科学”又是什么意思呢?而当你问“他们的这种相信是价值还是事实呢?”这种提问方式就预设了一个前提:任何陈述不是事实的就是价值的,但这个前提并不成立。因为人的想法、陈述或者判断,有许多分类的方式。“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只是一种分类,但这不是唯一有效的分类方式,也没有穷尽所有的陈述。有时候这样提问并不切题。 就你关心的问题而言,可能另一种分类,“信仰”与“知识”的区别可能更相关。比如,知识论中JTB理论就是一种(认为知识就是justified true belief[正当的真实信仰])。上帝存在是一个信念,但这是一个JTB吗?要真正讨论这样的问题,就进入了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领域,这需要另一门课程才能完成。 “我相信我理解了你的问题”,我在表达一个信念(belief)。然后你不同意,说“老师,你误解了我的意思”。那么,如何判断我理解了还是误解你的问题呢?是依据你表达出来文本,还是依据你想表达的意思呢?这里你会发现语词的涵义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语言哲学。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