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马尔库塞III:“实质性的变革”是有可能的吗?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来和我一起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上一次讲到,马尔库塞说,社会的变革,只有物质和技术进步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做出“ 实质性的变革 ”,用他自己的话说,社会需要的是“质变”而不只是量变。
但问题是,就算变革是必要的,可是变革真的可行吗?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矛盾那么尖锐,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被彻底颠覆,在当今更富裕、大众生活更舒适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变革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这正是马尔库塞反复思考的一个难题,他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乐观。
消失的革命主体
首先,革命行动需要主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有潜力的革命主体是工人阶级,可如今,革命的主体似乎已经消失了。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
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动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与他们的老板享受同一种电视节目,光顾同一类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有时尚的打扮,如果黑人也能开上一部凯迪拉克轿车,如果他们都阅读同一种报纸”,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 这当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但却表明不同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需求和满足,而这种需求和满足恰恰有利于现存制度的维护 ”。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到心理层面。 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异端”是如何被收编的?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当代的美国人,他们很可能会质疑,难道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和谐一片了吗?可是我们明明每天都能看到各种质疑、辩论、批判、抗议,社会并没有消除这些异端思想和反抗力量啊?
对此,马尔库塞也承认,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 他认为,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票,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 这就好比是,一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踢前锋,或者后卫?
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
马尔库塞的这种分析批判能令人信服吗?许多人都表示怀疑,认为他的批判方式看上去好像很深刻,好像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只是一种说辞。
我最初也觉得,他的观点只是“貌似深刻”,但后来我考察了一个真实的现象,想法有所改变。现在我把这段思考分享给你,然后请你来判断,马尔库塞的观点,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洞见。
这个现象就是摇滚乐。西方的摇滚乐(Rock and Roll)在1950年代中期兴起,1960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披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
19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且鲜明地针对政治,积极介入到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抗议等等。摇滚乐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力和号召力,又如此激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对吧?
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巨大财富,进入上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所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段话。他说, 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排斥消灭掉;要么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没有希望的希望在哪里?
你看,虽然马尔库塞坚决地要求变革,但他也深刻地理解到,要让变革发生,难度非常大。曾经明确的革命主体消失了,而其他的异端分子很容易被体制“收编”。要想实现他所期望的“质变”,似乎希望非常渺茫。
但马尔库塞并没有放弃变革的希望。就像马克思一百年前曾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马尔库塞也说,“ 解放的幽灵 ”正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徘徊。
首先,他看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巨大的内在矛盾。比如,在1960年代,帝国主义扩张造成的全球冲突,核军备竞赛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持续的不平等,还有不断加剧的人的异化……这些危机显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消失,它所维护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统一只不过是幻觉。
但幻觉不可能没有裂痕,“解放的幽灵”就潜伏在裂痕之中。 马尔库塞剖析这个社会,致力于揭穿这种欺骗性的统一,就是要把裂痕撬开,将解放的幽灵释放出来,在思想层面上为变革创造条件。
可是,在工人阶级被收买之后,变革的主体在哪里呢?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于体制的边缘人群,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流浪汉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不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收编,他们的抗争虽然缺乏自觉意识,但这些被压迫者的抗争,最有可能撕开体制伪善的一面。
马尔库塞希望,这些自发的反抗和斗争,能够从他的批判理论中汲取思想养分,产生出自觉的政治意识,再进一步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他呼吁一种“大拒绝”,呼吁人们去否定现状,不再沉湎于消费和享受,用“变革的主体性”来取代“消费的主体性”,让抗议和反抗演变为真正改变世界的解放运动。
但是,尽管怀抱如此宏大的期望,对于运动的最终结果,马尔库塞并不乐观。 他说批判理论并不许诺成功,但仍然怀有希望。 在《单面人》的最后,马尔库塞引用本雅明写下的一句话:
“只是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人,我们才被赐予希望。”
“没有质变”的变革有意义吗?
好了,听了这么久,你可能也发现了,马尔库塞一直说要变革,但却没有指明变革之后该怎么办。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却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设性目标。
还记得前面的例子中,那个要求变革足球运动的守门员吗?马尔库塞可能会说,守门员变成前锋,这不是实质性的变革。那怎样才算实质性的变革呢?大概在足球场上游泳才算吧?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实际上,马尔库塞也没有提出任何可实现的制度性方案。
站在今天,我们来回看1960年代那场席卷世界的青年抗议运动,它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后来还引发了保守主义的强劲反弹,尤其体现在里根-撒切尔时代的经济政策上。
不过,这场运动仍然带来了重要的文化变革,在种族、民权、社会正义与平等、女权、以及性别和性取向这些身份认同的领域,几乎全面改写了传统的主流观点。1960年代的运动造就了整整一代“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持续在校园和公共领域中发出批判性的声音。
问答
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来评价这场运动的成败呢?按照马尔库塞的标准,运动并没有实现社会的“质变”,但它算是被收编了吗?还是说,即使没有质变,它仍然带来了一些有意义的变革呢?这个问题,我想留给你来思考。欢迎到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编辑按:27、28、29讲的小加餐,刘擎老师已经发布在知识城邦。
第二十二次小加餐,老师分享了他写的一篇影评,评论的是2008年的一部电影《革命之路》。
这是一部讲述婚姻的电影,却与1960年代的西方抗议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都知道,这场运动最终归于平静。
在影评中,老师写道:谁断送了革命?或者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戏梦”?我们就此可以“告别革命”而心静如水了吗?
对于这几个问题,老师给出的回答是怎样的呢?请你→戳这里观看。
划重点
1、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到心理层面,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
2、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异议,包括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无法突破体制本身,甚至掩盖了这个单面社会的真相。
3、马尔库塞说,在控制模式中,违背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排斥消灭;要么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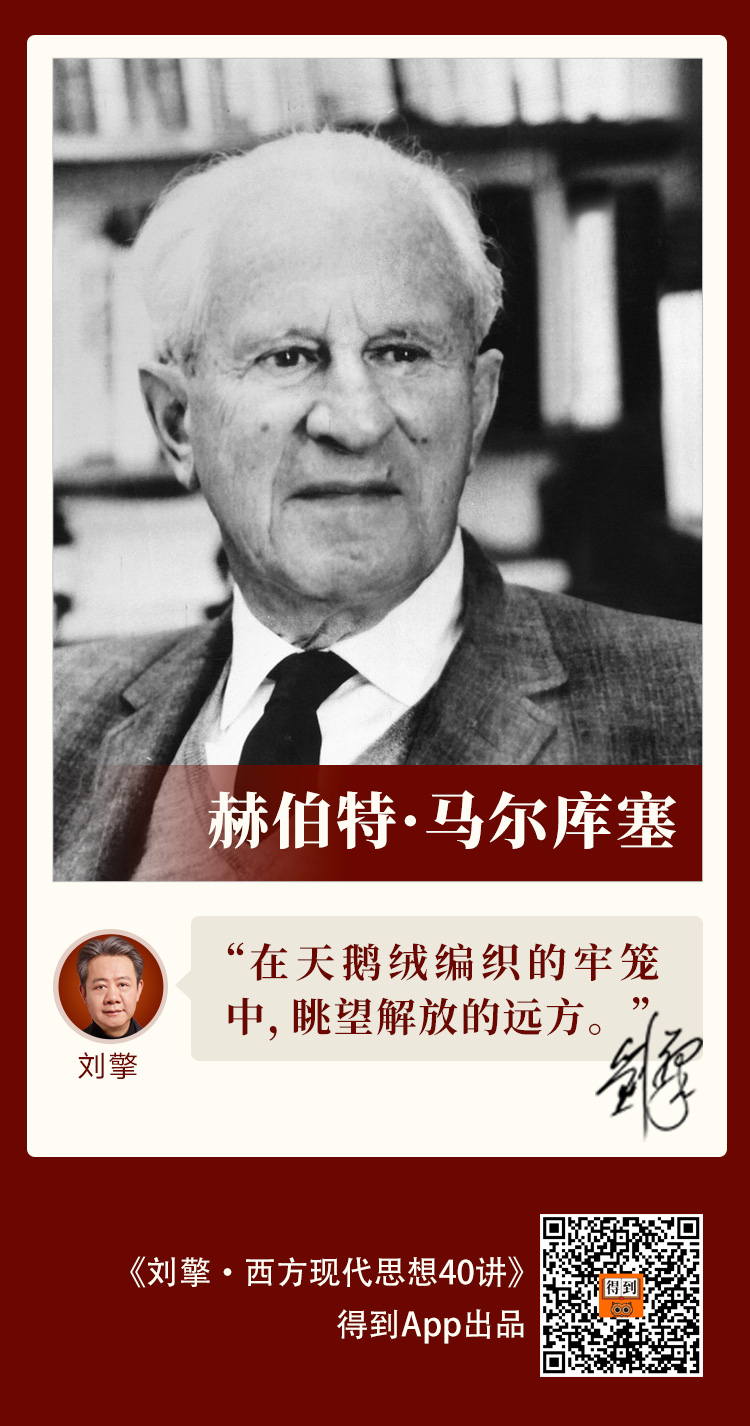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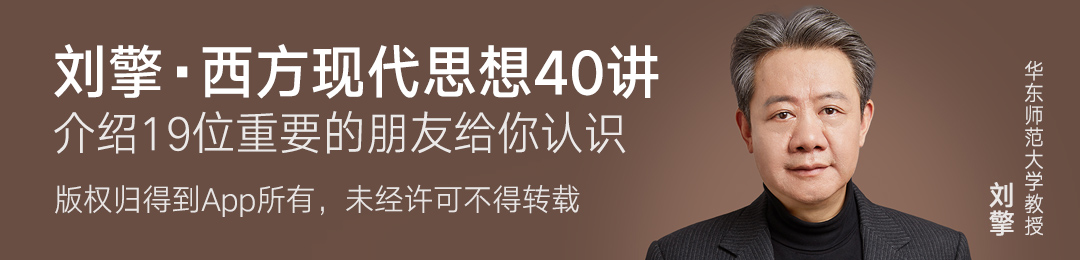
热门留言
熊逸:关于摇滚乐的例子,作为一个曾经的摇滚乐迷,我有几句话想说。
首先,把摇滚乐当成反抗力量,怕是误解。
绝大多数摇滚乐手的所谓反抗,无非只是青春期的发骚发浪,宣泄荷尔蒙而已,为反抗而反抗。 即便他们生活在马尔库塞亲手描绘的乌托邦里,假如真有这样的一处乌托邦的话,他们也会拿出同样的劲头来反抗的。
退一步说,就算他们真对自身所处的体制有任何不满,想要借助摇滚乐来宣示反抗精神的话,我们也必须想到,这些小年轻既没有足够的社会阅历,也没有认真读过几本书,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可以是美的,我们欣赏艺术之美就可以了,或者假如我们仍然年轻的话,跟着他们的音乐嘶吼,发泄我们过剩的荷尔蒙和各种压抑、不满也就是了,但绝对不能把内容当真。
并且,歌词所表达的反抗内容其实远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只是音乐本身。只要音乐出彩,歌词就算换成爱国爱体制的内容也一样会大红大紫。而音乐本身是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纯形式,所以才会在古典美学当中受到追捧,被奉为所有艺术形式当中的最高级的形式。 纯形式不需要内容,或者说填上任何内容都不会严重地影响纯形式的艺术感染力。这就意味着,摇滚乐未必真是被体制收编的异端,它仅仅是纯形式上的异端,如果需要作为异端被收编的话,也应该是被传统音乐收编。 所以,对于资本主义体制而言,它其实既不是异端,也不是正统,两者并不存在真正的瓜葛。
Cduoduo:“要么被主流社会消灭,要么转化为体制的一部分继续存活”——感觉《黑镜》第一季的《1500万》简直就是对照着设计的: 一个阶级夸张分层的封闭世界里,80%的人劳动以“生存”,10%跟不上节奏的人彻底边缘,而这两者创造的价值都用来满足10%只享受不劳动的顶尖群体。 男主失去爱人后变成革命者,以利刃抵着自己的颈脖,疯狂地控诉这个体系的疯狂……体系从中窥见他的“新鲜”劲儿可以为己所用,诱惑贿赂他……最后他和自己痛失的爱人一样,成为体系里更高级点的工具,原来的武器成为他的道具,刀抵着脖子控诉成为他随时演的姿态。
在足球场里游泳不是变革的本质,变革最关键的不是“为了变”,而是“为了什么变”“变成什么”。 就像组织在设定“变革指标”的时候,那些数字本身没法提供真正的驱动力,那些数字指向什么、抵达什么才是人们想看到的。
我觉得驱动力在于“真正想要什么”的渴求,在于总觉得“哪哪儿不对”的躁动,在于那些裂缝中的声响、歌舞升平下的虚空感。
量变是能够推动质变的,即使慢一点轻一点,也在等待那一刻到来。
陈C:结合前两讲,消费社会下民众被舒适的生活所“贿赂”是事实,产品创造了需求也是事实,表达不同声音的人被“售卖”还是事实,很多人将劳动视作苦役而非实现自由与个人价值的方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而在这样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原本应该起来反抗的工人阶级,都享受到了“舒适生活”的便利,甚至亲身感受着阶级的同化。从马尔库塞的角度来说,反抗确实是越来越难了,甚至要从“边缘群体”开始着手了,反抗的前景并不乐观。
但是如果借助之前讲过的,尼采的“视角”理论来看的话,事实的认知就是不同的,对上述所有事实的描述将会是另一个样子:民众基本上告别了贫困,而且生活越来越舒适,需求能够在商业社会中得到很大的满足,创新还为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更大的空间;社会中也有人表达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被听到,就会促使法律、制度与社会福利的改善,更多“边缘群体”的利益将会被照顾到,社会将更加平等、和谐;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激烈的批判,也是对社会的警醒,他们是维持社会多样性的重要力量,能促进社会的反思(某种意义上讲,主张反抗的马尔库塞,也是这样的“反对声音”之一)。
制度必怀缺漏,社会总有不公,问题一直都有,只看如何对待。现实是,如今这个“贿赂”民众,又给民众一个发泄的出口,并伺机“收买”不同意见者的社会,人们已经离不开了。而一同发展这样的社会,让它更加舒适,尽可能照顾好“边缘群体”,同时也为多样性留有足够的空间,这符合多数人的切身利益。所以现阶段再谈“反抗”,不仅没有可操作性,可能也并无益处。关键还是在于,努力工作、享受生活的同时,也要明白,我们需要反思与质疑,不时要用带有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社会,也审视我们自身的生活。
王黎璐:马尔库塞认为要改变这个社会需要通过一个总体性的革命才能实现,只有这个总体性革命才能否定、破坏和炸碎操作原则——现实原则的现行历史形式。而当这个总体性的革命由于主体的缺乏并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就把希望寄托在一些较小的否定力量上,例如第三世界中的一些解放运动,盼望这些运动有朝一日能够与发达资本主义内部革命一起汇成一个总体性的革命。但正像R.J伯恩斯坦指出的那样,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60年代的国际新左派运动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的天真,一旦‘满足的理性’在一个质的不同的世界胜利的幻想和美梦不能马上兑现这一点变得清楚时,其中许多人就准备在其他方式中寻求满足”。理论的立场不能是一种纯思辨的立场。它应该是一种历史的立场,应该立足于既定社会的能力之上。
佛祖门徒:资本主义体制对于摇滚乐商业化的历史让我想到技术理性和市场权力对于当今发达工业社会的控制。 何谓“技术理性”,意即现代技术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和影响文化的过程中,由物质手段、工具操作和科技逻辑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力量。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着眼当下,“技术理性”快速而又无情的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深厚底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消解作用。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精神价值已经被技术理性所支配的大众传播媒介从理想的王国中拉下来,精神文化开始甚至已经从属于物质文化,变成物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何谓“市场权力”,意即市场在现代商品社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商品化逻辑已经渗透进社会每一个领域,同时包括哲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之中。这样带来的结果有两种,一是将精神文化变成可供出售的商品,二是精神文化对于既存现实不再具有超越性和反抗性不,更多服从于市场行情和买卖交易,其最本质的东西也就从此丧失了。 技术理性和市场权力的协同作用,不仅使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失去了独一无二的个性和价值,更使得其独特性和自律性向既成现实妥协,失去了原本那份蓬勃的生命力。
裘德:这一篇的结尾,特别适合接着看老师写的那篇革命之路影评,老师发在知识城邦的小加餐22里了。我把链接放在了知识账本的上方,提醒大家看看,错过真的太可惜啦。
王宇晖:老师,我有一个困惑: 为什么非要变革呢,如果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根本就在享受这种异化,这种奴役,这种不自由,这个时候有的人突然想着去拯救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你们是被异化的,来,看这边,我会给你们更好的生活,更接近人的本质的生活。 这个时候大多数人会怎么看待这些救世主呢?我活的好好的,你凭什么来拯救我?我明天还要享受消费,我觉得这样生活非常好,你自己一边玩去。 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变革,真的必要吗? 还有,关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我觉得量变是可以引起质变的。如果马尔库塞设想的,自由的,没有异化的社会是终极目标,那我们现在这样琳琅满目却又有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的社会,是否算是终极目标的某种初级阶段?由于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没法直接地,激进地引发质变,只能慢慢拱。 亦或者,悲观一些,所有的量变的范式一直还是框死在当前的社会框架之下,所谓的改革力量和异端学说,只是社会为了维持好看的,琳琅满目的,有百家争鸣外壳的样子,而故意放水放出来的呢?
davidx:马尔库赛的思想是听课程到今天最不赞同的一位。 感觉他看问题太主观,就像顾老师说的刺猬,比如收编这个说法,至少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可以是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给了有才华的人,有被他人所欣赏的价值的人,通畅的上升通道。 个人感觉马尔库塞就是那种大而无当,脱离实际的左派思想家。
新手上路:昨天的课程下来积攒了许多的困惑: 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充分享受着物质自由的现代人为什么学习看似落败的马尔库姆的思想呢? 无法撼动那些装睡的中产阶级,是否马尔库塞的呼喊失去了意义了? 马尔库塞那西西弗斯式的无望,是悲壮荒谬吗? 人类研究鸟儿飞行,并非为了指导鸟儿,通过研究鸟儿人类发明了飞机。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剖析,虽然没有引发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但给人类社会指向了更高级的目标。这不,他使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成为现实。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改变,引发这些改变的,正是马尔库塞式的西西弗斯们,他们洞见了旧世界的虚弱并无畏地撬开缝隙,让人类进步思想的光辉照进去。 表面看来马尔库姆是一个落败者,所以在课程开始,始终揣摩着刘老师课程安排的意义,直到看到这一句“批判理论并不许诺成功,但仍怀有希望。” 思想无声无息地滋养人类,像水之于鱼儿,空气之于鸟儿。我们内心都保留着一个梦想,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感谢那些思想家。 得承认,刘老师精彩的课程让马尔库塞的思想照进了我的大脑。
高阳:我觉得他犯了一个隐秘的错误 他觉得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收编,其实反了
是资产阶级的老板们也和工人阶级一样被资本奴役了
这场戏的坏人是资本而不是资本阶级。
作为工人阶级都被贿赂的不成样子了,资产阶级不更事被贿赂傻了啊?
作为资本的钱就像是一个生命体一样,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或多或少在屈服于这个主体。ceo和工人都在屈服被奴役,资本是有灵魂的就是变得更多。人类需要不需要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解决资本这个坏人还是要从钱这个主体本身去解决。总找一帮人去反叛另一帮人,这其实是可怜人打可怜人,最后都是更可怜。
坐井闲话:老师,在这节课中我有一个自己的模糊的想法,我认为本质性的革命存在,但革命的力量并不是人而是科技。 科技的发展带动物质的丰富,人们的生活与使用的工具因此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也会推动人的认知和思想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出现具有预见性的先知思想。 而先知思想能引发革命,往往需要物质条件和大众的思想及需求演进到转折点上,那时社会才能发生本质性变化。
佘天俊:当工人和老板享受同一种电视节目,甚至和总统吃着同样的汉堡,和世界首富喝着一样的可乐的时候,究竟是原来的阶级划分方式,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社会环境,还是说工人阶级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呢?无产阶级有产了,并不是以前无产阶级这个划分不对,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欺骗性,这是不是也有种,不管现实如何,理论怎么样都对的盲目性。 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要么会消失,要么被同化,这也是进化的普遍现象和规律,或者无论观察什么复杂系统,上面这样的现象都是普遍的,而每一次突变都可能会最终改变系统的方向。资本主义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并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概念和阶级,过去的阶级矛盾在新的社会发展水平下,不复存在,是系统的变化,而不是过去矛盾的具有欺骗性。 当工人阶级不再可能是变革的主体,把希望寄托于学生,失业者,流浪汉,这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这不是彻底的在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么。
肥老太婆:XS29 变化的时代,任何聪明的一方都在改变,资本主义除了将自己的保护色与环境融合得更好,还给予对立方以及其它层级一定的希望。历史早已让人们发现剥夺一切只会激起绝望后的义无反顾的斗争,而一丁点儿微弱的希望却足以迷惑既得少许利益者与拼命挣扎向上的其他阶层。集中营里那些“有技能”就能暂时存活的犹太人,有许多就是带着渺茫的希望却走进了毒气室。 马尔库塞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可实现的制度性方案,但已经在大众的心里埋下了种子,他点燃了变革的火种,即使前路崎岖,也有那微光照亮方向。
哦:对马尔库塞又爱又恨。他指出了消费时代人被“异化”的弊病,还在这条路上探索反抗之途,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具体反抗,反抗后又会是怎样的世界。从动物性和人性角度出发,我们无疑是在现代社会的轮轴中“异化”了,应该走向一条更为“人”的道路。但马尔库塞只说,此路不对,走这一条。而你再问这条路上有什么,通向哪儿,他给我们一个神秘的微笑。
李炜:刘老师引用马尔库赛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似乎堕入了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陷阱。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和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太不一样了,如果说马克思的确指出了那个时代下资本主义深切的内在矛盾,那这些矛盾是否还适应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本事是个巨大的问号。不能因为都叫做“资本主义”就都先入为主地用既有的、固定的“本质”去定义。
吴桐:马尔库塞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他反而在反人性。他的理想主义反而会带来灾祸。
西西弗斯:“实质性的变革”的发生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多数人的觉醒,另一个是发现更好的"选择”,回观历史每一次大的变革,都是对现有制度的不满,对新的“革命愿景”的渴望。在现有的这种“舒适”的体制下,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觉醒的,如果不拿出更好的条件,只凭现有制度的缺陷,是无法推动“实质性的变革”发生的。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有这么强的韧性,外在原因是它没有强大的“敌人”,内在原因是民主政治提供的”自我升级“条件,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异端”通过质疑、批判、竞争、投票等手段指出体制的缺陷,然后体系进行自我的完善升级,同时完成了收编的工作。
我们不能说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就是无意义的,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前提,其内在的自我升级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变革,对于不愿觉醒的人,在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条件的同时,设法升级其中的弊端,这无疑是成本最小的变革,也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已经觉醒的人,体制对其的控制作用也失去意义了。
Paux:劳动的异化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恶果,不如说是上帝死后的信念崩塌。同样的工作,有的人说我在砌砖,有的人说我在造墙,有的人说我在造教堂,有的人说我在赚钱让家人更加幸福,有的人说我在让周围的人快乐安定——一切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判断。
马尔库塞没有变革的方向,因为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曾经统一的普世价值已经被打碎,新的令大多数人一同信仰的价值选择在科学理性的光辉下无法再出现。
何紫朝:谢谢老师的分享。
感觉今天是马尔库塞的最后一讲,这三讲听下来感觉马尔库塞就像是罗胖原来说的,给时代唱挽歌的人。他可能在怀念那个知识分子独立高洁的时代,怀念你的思想都不那么整齐划一的时代。
但是他自己可能也已经感觉到,现在科学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人类的目前的生活方式可能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变革,所以他除了提出批判之外,并没有给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但是我个人感觉,现代化的时代,从宏观上看确实是越来越统一了,但是如果深入到细节去看。多样化的生活还是存在的。我是一名硕士生,很钦佩我的导师。上一讲,在听到人的异化的时候,作为一个反例,我马上就想到了她。即使是周末,她也会经常去办公室。就像现在疫情当前,虽然学校没有要求,她也每天坚持去办公室办公,感觉她并不是为了挣钱或者取得一个学术地位(实际上她的学术地位已经很高了),而去工作的。我觉得,现代社会,相比于过去,“完整的人”在数量上估计也是越来越多了,只是在比例上越来越少了。
Fairyの乔巴:半年后二次学习。觉得马尔库塞的作用,仅仅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满意,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至于这条路怎么走,他不知道;是阳光大道还是充满荆棘丛生,他也不知道;是通往天堂还是走向地狱,他还是不知道。可能还有路,仅此而已。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