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桑德尔:当代人需要为历史事件负责吗?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来和我一起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这一讲,我们要认识的哲学家是迈克尔·桑德尔,他是我们课程中出现的最年轻的思想人物。
“就像上帝亲自给我打电话”
桑德尔这个名字,你可能早就知道。
还记得几年前著名的“哈佛公开课”吗?其中有一门特别受欢迎的课程,叫做《公正》。这门课在哈佛已经开了20多年,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桑德尔就是这门课程的老师。
2007年,我到美国访学,专门到哈佛大学拜访了桑德尔,在现场观摩了他上课,还对桑德尔作了一次访谈。
桑德尔在学术界的“成名之作”,和罗尔斯有关。还记得罗尔斯吧?他就是前面讲过的《正义论》的作者,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桑德尔在牛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他的论文对罗尔斯的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论文修改出版之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辩论。
桑德尔也就在这场辩论中脱颖而出,成为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的标志性人物,那一年他才29岁。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桑德尔回到美国,到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而罗尔斯恰恰也在这里工作。你可以想象,面对一位比自己年长32岁的大哲学家,又是自己批评挑战的对象,桑德尔肯定是“压力山大”啊。我就很好奇,桑德尔和罗尔斯第一次见面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桑德尔告诉我,那简直是一个传奇。那时他刚到哈佛不久,一天,桑德尔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是约翰·罗尔斯”,接着就开始拼读自己的姓氏:“R-A-W-L-S⋯⋯Rawls”。桑德尔当时就晕了,他说这种感觉,“就像是上帝亲自打电话邀请我共进午餐,还特意拼了一遍他自己的名字,好像生怕我不知道他是谁。”
桑德尔被罗尔斯的谦逊深深打动。虽然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罗尔斯理论的批评意见,但他对罗尔斯本人抱有最深的敬意。
那么,桑德尔究竟对罗尔斯的理论提出了怎样的挑战呢?我们从他自己举过的一个例子说起。
当代人应该为历史事件道歉吗?
有一个你可能听到过的话题: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为历史上的罪责道歉?照理说,这是一个完全正当的要求,比如德国应该为二战时纳粹的暴行道歉,德国政府也确实这样做了。同样地,美国应该向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道歉,日本也应该为侵华战争道歉。
国家需要为历史罪责道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还有人反对吗?真的还有。比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就反对向原住民正式道歉,他说“我并不认为当代的澳大利亚人,应当为前辈人的行为道歉。”
这种话听了会让人气愤,但你别着急,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说当代人不应当为前辈犯的错道歉,理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宣称,“人不应该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负责”。如果这样,有些日本的年轻人也可以说,日本侵略中国确实很罪恶,但那是我祖父那一辈的罪行,我既没有参与,也根本不赞成,为什么要我来道歉呢?
你看,对于这样的理由,你该怎么来反驳呢?
说到这,请该请桑德尔出场了。他认为,“当代人不必为历史负责”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要反驳这种观点,我们首先要看清楚,它背后的依据。
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
那么“当代人不必为历史负责”的依据是什么呢?桑德尔说,这其实是一种道德理论,叫做“ 道德个人主义 ”。
什么意思呢? 道德个人主义,就是相信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都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自主选择自己的目标,只需要为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个人道德责任的来源只是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群体、习俗、传统、历史……都没有关系。
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个人就没有什么“集体责任”可言,也就无需为历史事件承担责任。
但桑德尔说,道德个人主义是错误的道德理论,因为它所依据的“个人主义”观念是错误的。
在桑德尔看来,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是将单独的个体作为所有理论出发的原点,但自由主义却没有认真探究,个体究竟从何而来?
桑德尔认为,个人并不是先于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子,作为个体的“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被造就的,是被生活的共同体塑造而形成的。 共同体的英文是“community”,这个词也常常被翻译为“社群”,可以指家庭、社区,或者学校、工作团体,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这种大的社群。
在这里,桑德尔就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被称为“ 共同体主义 ”或者被翻译成 “ 社群主义 ”。就是强调,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再由个人组成社群。
桑德尔引用了另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太尔的一个观点,他说, 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 。如果你要回答自己是谁、需要什么和想做什么,这些问题,答案就在你的故事之中,只有讲通了自己成长的故事,理解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和需求,你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故事。离开了 社会关系 的塑造,你就讲不通自己的故事。
比如,你的母亲是一位工程师,家里订了些科普杂志,你从小就爱读这些杂志,高中就选了理科;而你特别喜欢的物理老师还是个科幻迷,在学校搞了个科幻文艺的兴趣小组,你在小组活动中写了篇科幻小说,老师同学都大加赞赏。最后你高考没去考理科,而是考进了电影学院,学编导专业,梦想是要拍出最棒的科幻电影。
桑德尔认为,只有讲通了自己的故事,你才能解释自己生活中的选择有什么意义。而意义无法从个人独立的自由意志中产生。你的故事是在社群的关系中塑造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明白彼此的故事。这就是社群主义的个人观。
个人真的是“原子化”的吗?
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桑德尔为什么会质疑罗尔斯。
还记得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吗?就是大家在无知之幕后面,会忘记自己的所有特殊性,一起来商议签订一个社会契约。桑德尔会说,无知之幕背后的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完全一样,其实就是一个人,是毫无个性的抽象的个人,也就谈不上一起来商议社会契约了。
桑德尔认为,自由主义的这种个人观,首先把个人看作是孤立的原子,完全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独往独来,他称之为“无所牵绊的个人”。他认为,这是对个人的错误理解。
由于这种错误的个人观,自由主义对社会的理解也错了,只把社群看成是工具。比如诺齐克,认为国家只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如果只是工具,那个人和国家之间也就谈不上什么爱国情感和忠诚了。就好像你不会说,我爱一把剪刀,我要忠于这把剪刀。
再比如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比诺齐克要温和一些,认为社会是一个合作互惠的体系,人们在合作中会产生善意和情感,建立共同的价值。但桑德尔认为,这种情感性的社群仍然没有真正的相互依赖,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团结。你想啊,恋人之间也有感情,要分手还是会照样分手。
社群“构成”了个人
那么,桑德尔的主张是什么呢?
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 更重要的是,社群的纽带关系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 用桑德尔的术语说,社群是 构成性 的,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
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和社群有着紧密的纽带。 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有了归属感,知道了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么紧密的关系,那么你也就有了一种“ 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 ”。
这种义务和前面说的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就很不一样。 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一种由于个人选择带来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了契约而形成的义务。 桑德尔说, “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你在这个社群中成长和生活,这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它并不需要你的同意。
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
其实你想想,你并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吧,但你是不是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呢?这就是你作为家庭这个社群成员的义务。同样,在国家这个社群中,你会继承前辈的遗产,同时你也被赋予了一种责任,要为历史上前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原子化的个人观从何而来呢?
最后,在和桑德尔的谈话中,我向他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社群对个人的塑造如此深刻,那么,当下流行的那种原子化个人观,不也是社群造就的吗?为什么社群会塑造出这样一种脱离社群的个人观念呢?
我没有从桑德尔那里获得满意的回答,而这就是下一讲要探讨的问题。
问答
当然,如果你愿意尝试回答这个艰难的问题,请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见解。
划重点
1、道德个人主义,就是相信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都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自主做出选择,也只需要为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
2、桑德尔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观把个人看作是孤立的原子,完全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独往独来,无所牵绊。他认为这是对个人的错误理解。
3、桑德尔主张,社群不只是工具或者情感依赖,社群是构成性的,它的纽带关系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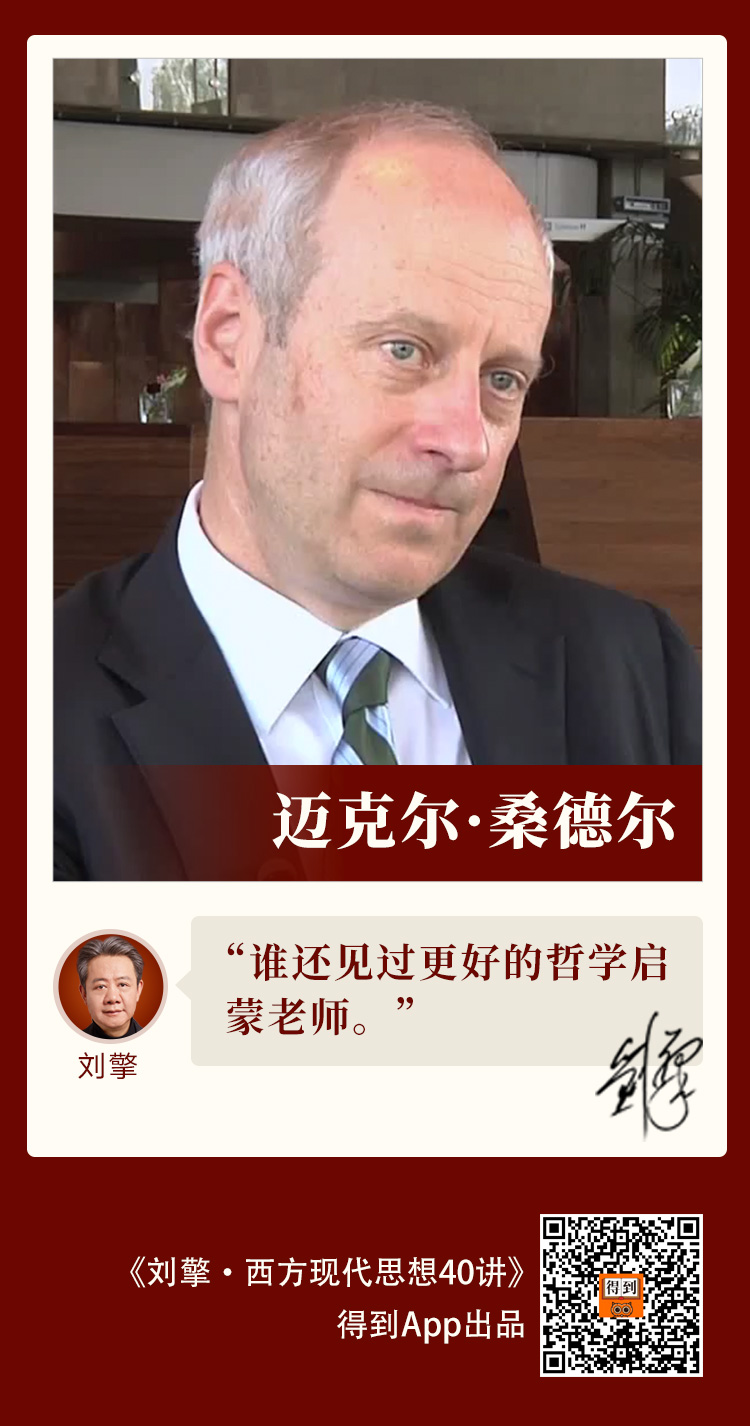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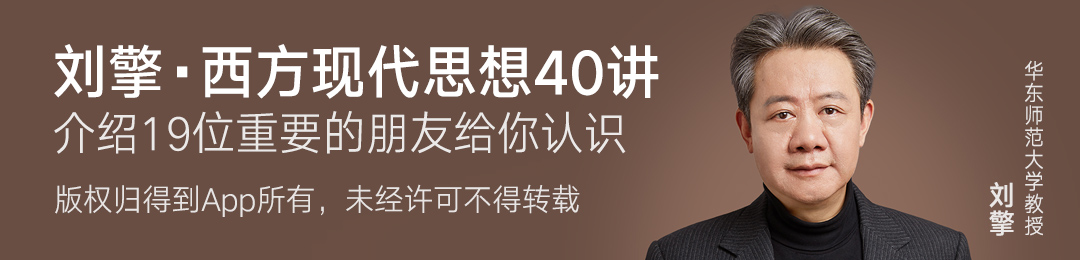
热门留言
熊逸:“其实你想想,你并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吧,但你是不是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呢?”——我觉得并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我之所以赡养父母,仅仅是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义务。
我并不觉得我有这个义务,谁也不能强加于我。如果法律非要强加于我的话,我虽然必须服从,但心里并不认可。
比如从社群主义角度的意义来说,汉朝要看匈奴人,就觉得他们“贱老贵壮,气力相高”,他们毫无赡养父母的义务感。桑德尔对此会怎么想呢?
但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觉得确实存在赡养父母的义务,而他们不曾想到的是,这个义务只不过是来自习惯和社会的压力而已,这就见得出桑德尔其实混淆了实然问题和应然问题。
社群主义如果并不作为一种主义的话,那么它所涉及的内容仅仅是一个实然问题而已。在事实层面上,它确实是成立的,但是,难道因为事实上的成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证明出在价值观上的成立吗?
以上几乎所有的现代思想家都会混淆实然问题和应然问题,从事实如此论证出应该如此,这明明就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嘛。我觉得他们的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思而不学则殆”的缺点,尤其是缺乏在探究价值观的问题上非常必要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眼光。
我觉得,所有的价值观问题,当你想搞清楚它从何而来的时候,那么它就属于实然问题,而当你想宣扬它的时候,它就属于应然问题,而所有的应然问题分明都可以彻底摆脱实然基础,或者说摆脱人类的生物性基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讲的其实是一个应然问题,而桑德尔对他的批评却是从实然角度进行的,不应当。
曹玉彬(贤君口腔):编辑啊,努点力,我觉得这个课卖不到五万是太不应该了。没有一个课用如此精炼,如此少的内容就能描绘这么多丰富的思想的,而且,还前后连贯,像大神对垒。思想连续剧。
刘擎(作者) 回复:编辑也很发愁……
Edmund:1.我认为这种矛盾的源自于,当我批判自由主义导致了原子化的个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自由主义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也就承认了自由主义对社会的描述和定义是真的,而我再批判自由主义那种无所羁绊的无根的自我是不符合现实的,声称人是有机的是共同体的一份子,共同体本身是人的构成性要素,这也就在事实层面上否定了自由主义对社会的的描述和定义,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就产生了。 2. 我觉得社群主义对个人主义批判,一个大前提是个人主义天然排斥共同体。但我认为个人主义并不必然反对共同体,共同体内多元个体的存在对以及这种存在长远看更有益于共同体这一事实,就是很好的例证。 3.共同体的影响当然存在,但并非是决定性的,社群主义告诉我们: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只不过这个网得有机的挂在社会共同体这个枝桠上。但毕竟价值和意义的具体实践者和担纲者是只能是有思考能力的个人,而人的思考对象应当也可以指向共同体的,并且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我们跨越共同体帷幕去“开眼看世界”后,我们的视野和思考才会进一步打开,我们的自由才会得到拓展。
刘擎(作者) 回复:你好,我是这门课的编辑。第一点很敏锐!下一讲本来有一部分内容就是要讲这一点(沃尔泽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的批评……哈哈这串字打出来就有点让人发晕了),不过篇幅所限去掉了。看老师会不会在加餐里放出来吧。
淸风徐来:听了桑德尔的思想,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起点:我的思想从哪里来?我还有个人的真正自由吗?
首先我得承认,桑德尔的主张很有道理,是社群“构成”了我这个人,确实是社群的纽带关系从根本上定义了我是谁,它塑造了我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情感与责任意识。我喜欢中国这片热土——喜欢吃热干面,喜欢唱茉莉花,喜欢仰望飞流直下三千尺,喜欢欣赏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喜欢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这些的确是我的身份认证,我知道中国人的孝道,中国人的仁义礼智信,中国人的故乡情怀,以及她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然而,既便如此,难道我就没有独立而自由的思想了吗?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个人觉得,一个人所形成的思想应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桑德尔所说的社群给予我们的,也就外部环境传送给我们的一切信息,这些信息甚至是带有源头性的;一个是我们的头脑自我能动性的处理与加工。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的思想不是外部传送给我们的信息的物理叠加,而是要加入我们个体头脑的能动性加工,是外部信息与自我头脑起化学反应后的结果。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思想有外部信息的输入,甚或是源头输入,但并不能否认有个体自我的能动加工。也因此,个体的思想自由与个体自由,群体思想与群体合作才会长久互动、协同发展。正因如此,也让人类的未来显得鲜活、新奇而充满期待。
王黎璐:社群主义的权利理论不是反对个人自由,而是主张把自由放在其适当的位置;它也不主张取消个人权利,而是为个人权利划定适当的界限;它并不否认自我的个性,而是为这种个性的形成与存在寻找历史和社会的基础。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的第二版前言中表达了他对被贴上“社群主义”标签的某些不安。虽然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但他们个人并不是纯粹的社群主义者,至多是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更加注重社群而已。 俞可平说:“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实质上是互补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双方的侧重点和着眼点有所不同。”如果“离开发达的自由主义就无法真正地理解社群主义,离开自由主义谈论社群就会发生时代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结果很可能是危险的。”个人权利从其自身正当性而言,确实是通过社会承认而获得的,毕竟权利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由彼此相互承认的规则所认同的正当事物,因而权利是随着社会而产生和存在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没有人们相互结成的群体或组织即社群,就没有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就没有权利的出现。社群是孤独的个人的伊甸园,如果一个现代人脱离了社群与社会,他“就没有国家,没有城邦,他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不管他身在何处,他只是一个精神上的流放者”。 这种孤独的人,还有什么自由与权利可言?
陈C:桑德尔指出了社群对个人的塑造作用,这有一点像是心理学所说的“我是一切体验的总和”,但是在此基础上又更近了一步:构成了自我的“体验”,来自与环境、与他人(社群)的互动,以及对社群文化的继承。桑德尔的社群主义,等于是对“人从哪里来”进行了一次剖析。而也正是这种对人的根源的思考,动摇了罗尔斯用作其正义理论的基石,也就是“无知之幕”思想实验。如果“幕墙”以外的那些偏好、禀赋、出身的部分是我们无法割去的,那我们凭什么相信,自己真的能支起这道“幕墙”,又如何能凭借这个不可能成立的思想实验,来推导出罗尔斯的正义论呢?从这个角度讲,桑德尔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是能够动摇根基的,的确非常尖锐。
桑德尔指出的这种社群对个人的塑造,到底有多强的作用呢?我认为很强。如果说得极端一点,即便一个人不与其他任何人直接沟通,他的衣食住行,以及由这些所塑造的衣着品味、口味偏好、行为习惯与生活情趣,仍旧是所处社群给予的——甚至他“不与人何人直接沟通”的倾向,都可能是社群的造物。但反过来说,同样的社群环境下,既然有人选择消极地,不与其他任何人接触,也就会有人积极地融入;有人选择被动接受社群的影响,也就有人会尝试主动去改变它,个人还是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
综上,可以说只要我们作为“人”生存在这世界上,社群就是一种我们避不开的“客观存在”;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处在同一社群之下,我们也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哪怕是产生出否定社群作用的,原子化的个人观(能产生这种观念,也需要一些特定的社群文化作为基础)。个人受造于社群,其选择却并非总是受制于社群。
左星星:其实我不是很同意桑德尔的观点,如果我因为生活在这个社群中,就必须承担社群赋予我的义务,那这其实也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我的选择,而且关键是,如果按照桑德尔的观点,我根本就无法改变这样的义务,即使我已经离开了社群,我的想法和社群大部分人已经不一样了,哪怕造成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 → 教育
2019年有一本书很有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塔拉出生在一个摩门教的社群,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徒,反对孩子接受教育,反对现代医疗,有妄想政府迫害症,虽然作者说,她的父亲或许是受到了妄想症的影响,如果按照桑德尔的观点,作者塔拉就应该接受这个社区赋予她的义务 → 放弃教育的机会,跟着父亲在修车厂工作,然后继续重复父亲希望的生活
然而事实是,塔拉奋起反抗,在没有接受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的情况下,凭借个人的努力考取了杨百翰大学,后来更是到剑桥留学
塔拉的选择,也必须由她自己承担后果,这个后果就是,在她父亲的主导下,塔拉和所有家族的成员都断绝了关系,这或许也满足文稿中所提到的道德个人主义,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塔拉是坦然的,她也接受了这样的后果,而我作为旁观者的感想就是,如果觉得教育太昂贵,那么试试无知的代价
小陈同学:很好奇罗尔斯是如何看待桑德尔的观点的,而又为什么每个思想家都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少根据别人都批评改进自己的原有观点
刘擎(作者) 回复:当然会改进啦,前面讲过的很多学者,生涯后期的观点都是有所变化的,像是罗尔斯、诺齐克、沃尔泽还有前面的萨特等等等等。只不过一讲的篇幅有限,课程里主要还是讲思想家本人在思想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编辑)
头发末梢的遗憾:作为社会行动者个人主体,并非完全是由其所在共同体所决定的,不能同质化地去理解个人的行动以及行动决定。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条件下,不同的主体在同一种对话关系中,构成了不同的主体地位,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先验必然的。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既是被决定的,又具有自我决定的特性。
nick:听完之后还是很多疑惑,试着通过回答最后的问题来呈现这些疑惑。 因为桑德尔所描述的人与社群的纽带关系是重要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人类社会既存在强国家主义,又存在强个人主义,两者都在事实上塑造了原子化个人。 特别是纳粹这样的强国家主义,它看上去要求公民共同信仰一个至高善(似乎具有社群主义的意味?),但在社会生活上它要大规模培养原子化个人,从而抵制公民联合的社会共同体力量的壮大和公民参与形成的公共政治美德。如果把这样的“国家”也看做社群,那么这样的社群恰恰就是培育原子化个人的温床。 因此,“社群”主义的“社群”是否应该强调一下,这个社群是社会中的多元化小共同体?(也许把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当作共同体就不太妥当?)也就是说,社群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它的实现必须要求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一个强大的中间社会,每个人基于自己的认同和自由选择来归属某个群体,而这种归属或纽带也必须是自己可以改变,切断的。而只有经由个人的主观认同和选择,这种归属、依赖和热爱才是有意义的。同时,这样一种强大的中间社群也才能避免强国家主义的危险。 在这个意义上,社群主义的底色是不是还应该是自由主义的?
朱家乐:我认为个人是否应该为历史事件负责取决于他到底有没有从先辈的罪行中获取巨额利益。比如说当代美国人必须为当年大屠杀印第安原住民道歉。因为虽然今天的美国人并没有参与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但是美国今天的繁荣昌盛却离不开对印第安人的虐杀,所以现在的美国人从先祖那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那这时候就需要道歉。而反之,如果个人并未从先祖那里获得过任何有关罪行的收益,那就没必要道歉。因为他的手上并没有沾上罪恶所导致的收益。
肥老太婆:XS34 桑德尔强调了个人的社会属性,实际上也是自由主义个人去除的种种属性中的一个侧面。而这个侧面的确是作为公民、社会成员或者某种共同体成员的无法删除的真实属性之一。 先不论历史责任是否应该由现在的成员承担,至少条约下比如战争赔偿无论以国家还是怎样的名义,都需要一一履行。道德层面的非强制性责任,则往往有社会团体甚至是跨国界的人们自行承担。这也说明了良知以及责任,人们的社会属性并非都出于责任强制,还有对自身的积极反思,也是人性最光辉之处。
佛祖门徒:从表面上看,原子化个人观的表现主要是:对他们而言,外部世界和他人如同天边飄动的背景,关心和了解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旦身处原子化处境中,公共性和与他人的情感共鸣、思想呼应就会变得不再需要,仅有的沟通也仿佛自我独白一般,更多的时候不过是沉迷于个人私人趣味的简单重叠。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原子化的个人便丧失了客观地进行自我认识的兴趣,转而自我欣赏。狂妄自大和自恋自艾似乎都遵守同样的心理逻辑。 但我所感受到的原子化个人并非不需要关注和交流,他们的认知里不过是觉得孤独,无人能懂,所以主动拒绝与外界的联系。但在其内心深处仍然渴望遇到同类物种,只是求而不得,又觉得非生活必需,所以也就放弃寻找的希望。很多自认为“佛系”的人大抵如此。
西西弗斯:我不同意桑德尔的这种观点,桑德尔说“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你在这个社群中成长和生活。”我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正是由于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也无法从出生就选择自己的社群,才被动的生活在社群当中,然后我们会被社群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有好有坏,我们无法拒绝,直到我们有能力自己选择。我觉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对这种被动的选择负责吗?我们应该有选择吗? 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个婴儿从出生就被父母抛弃,那么他被其它人抚养成人后,他还有责任赡养他的亲生父母吗?我认为这时我们不应该在谈责任,而是要问他愿不愿意,因为是他的父母失责在先,这是他的父母选择的结果,他的父母有选择的能力,那么就应该此承担后果。除非婴儿有选择出生的权利,但是他没有,这不是他选择的结果。 但是如果要按照责任来划分,也很难划分的清,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家庭暴力的痛苦环境当中,父母带给他的没有美好,只有痛苦,那么孩子应该赡养他的父母吗?同样我们也要问孩子愿不愿意。按照桑德尔的观点,承担痛苦也是“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孩子必须赡养父母,没有选择。可是这个孩子他有选择不承受这种痛苦的权利吗?
正是”社会义务“对于个人这种强制性的被动选择特性,才导致个人观念的形成吧,根本的原因萨特已经说过,“人的本质就是自由。”
onetree:桑德尔从实然推导到应然的过程,疑问多多。我是社群一员,社群产生了我,塑造了我,故此,我自然的就应当承担社群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这个逻辑违背了认知直觉,并且把人工具化。1、责任必然是和人主动性相关,一个历史事件,我从没介入,何来责任?此为历史视角。从当下视角再看。假如我的社群侵占别的社群,我坚决反对,并尽了一切可能阻止这个罪行,那么,我在这件事情上又有何责任而言?? 2、一个生物学上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在精神意义上说,他并非全程是“人”。一开始他先是一个物,而后获得自我意志具备自我选择能力,他才算真正的“人”,从而承担起“人”的责任与义务。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再度丧失了自我意志和自我选择能力(比如植物人),那么他也就再次成为“物”。可以说,“人”是获得性的。如果责任和义务是由“人”承担,那么他们和“人”一样,也应当是“获得性”的,不存在天然的责任和义务。天然必需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人”,丧失了“人”的意义,那只是工具而已。就好比我们制造一个器物,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它都需要被作为工具使用。
豆豆:看到题目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和澳大利亚前总理一样,不需要。虽然觉得这样说不对,因为我们总是为日本人不肯为二战道歉而发生口角,二战对德国人总是一道不可触碰的禁忌。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为历史负责,需要为多久的历史负责呢?人类浩瀚的历史长河里面,民族之间的冲突是那么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宗教内部的,中原民族与外族的,如果计算起来,可能谁和谁在整个历史上都是有冲突和斗争的,最后还不都是自己为自己负责,只有少数人在同一个社群里面吗?
Bruce:如果我们倾向于相信个体的自由和理性,自然会认为当下的人不必为历史背锅。但考虑到现实情况下,我们是过去的产物,从思想和物质上受到的影响,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方面,不能像洗白了一样圣洁化,更不能太沉迷于负罪感。更值得做的是尽可能的客观认识和了解历史,尤其是承认对于当下和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规避可能出现的坏事,尽可能做好事。简单来说就是改正错误,但也要意识到我们可能会犯错,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青山:个人当然要为祖先负责。 因为我们也享受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好处——先进的技术、璀璨的文明等等。 我们不能只承认祖先的光辉而不承认祖先的错误
佘天俊:让人豁然开朗的桑德尔。 心理学一直说,人无法单独存在,人是活在关系中的人,没有被看见的就不存在。即使能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但总不能彻底感受到。直到看到今天这篇,社群构成了个人,而不是个人构成的社群。 作为单独一个原子的个人,和无知之幕背后的抹去了一切的人,的确无法称为人,所有的思想,身份,情感,都是某一个网络的一部分,都无法单独存在于所有网络之外。 “社群主义”,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再由个人组成社群。这句看似不成立的话,倒是一下破开了原先的迷雾,从点开始看整体,总是无法看清,而从整体出发看个体,反而能既看清整体,也看明白个体。 社群定义了你是谁,社群创造出了你的身份,创造出了你的思维,各种社群和网络,都是构建出你独特自我的一部分。 原子化的个人观,可能是社会支持系统过度发达后,产生的虚幻的感觉。仿佛离开社群,独自一个人是完全可以存在的,可以自我定义的,但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幻觉,是一种因为能够随时回到社群中,是一种对此笃信无疑的安全感,带来的原子化的幻觉。
平安与团团:老师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明确了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就是个人从自古以来的宗族式自然生活转变为工业社会机器模式中的非自然的“社会原子”生活:我们独自生活在无亲无故的大城市里,干着自己的工作,拿着应得的薪水,过着孤立的生活,传统社群生活是我们心向往却回不去的生活模式,多少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深陷过老家的人脉网络泥沼中后,又无奈的选择回来? 传统家族或村庄式的社群生活是在以前无声的塑造着我们这些个体,但脱离了传统社群的孤立的我们,在并无亲密纽带联接的城市却是要寻找独立的个人的意义。这是不是就是尼采、萨特他们能引起现代人共鸣的原因? 所以我是很认同社群先于个体存在并塑造了个体的理论,但它是有时间边界限定的:它适用于现代化以前的社会,而现代社会里的个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群”,是被“原子化”的,是需要相应的个人主义来赋予孤立的人新的意义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