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沃尔泽:“原子化的个人”是怎么诞生的?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来和我一起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2007年的冬天,我在哈佛大学与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会面之后,又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拜访了另一位Michael,就是今天要为你介绍的人物, 迈克尔·沃尔泽 。他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也被称为是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和桑德尔比起来,沃尔泽就是老前辈了。
沃尔泽出生于1935年,196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是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中间又回到哈佛工作了14年。1980年,他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为终身研究员。这个高等研究院在学术界的地位非常高,爱因斯坦生命中的最后20年就是在这里工作的。
1971年,沃尔泽在哈佛教书的时候,和另一位教授合作上过一门课,主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合作者是谁呢?就是那位才华横溢的狐狸型哲学家诺齐克。前面我们讲过,诺齐克是一位自由至上论者,但沃尔泽的立场偏左,属于社会民主派。两位教授在课堂上展开了精彩的辩论,学生们看得不亦乐乎。
可能是他们感到课堂上的辩论还意犹未尽,他们各自都去写书,把自己的观点充分阐发出来,结果产生了政治哲学的两部名著:一部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另一部是沃尔泽的《正义诸领域》。
沃尔泽发表过大约30部著作,其中《正义诸领域》,和另外一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都被视为当代政治理论的经典之作。在沃尔泽那么多作品中,我特别偏爱他的一篇论文,题目是《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所以,我在拜访沃尔泽教授的时候,刚刚坐下来不久,就谈起了这篇论文。
我向他请教,你能算是社群主义者吗?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还重要吗?他回答说“这种标签不适合我,其实标签对大多数学者都不适合”。他还认为,社群主义的批评总会再次反复,“但那场辩论已经过去了”。
我继续问他,“有人说,是你1990年发表的文章,终结了那场辩论,你自己怎么看呢?”。他笑着回答说:“也不能这么讲吧,不过我的文章可能起到了一点点作用。”
为什么我会对这篇文章特别偏爱呢?不仅是因为它在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很有影响,而且更主要的是,它帮我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一个大问题。
下面我就来和你分享,我究竟从这篇文章中获得了什么重要的启发。
“奇怪的”个人主义
那个困扰我的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个人主义怎么可能会出现?
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观念其实非常奇怪。它是假设,先有单独的个体,个体组成了社会,社会又造就了国家。但这种想法明显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我们的经验常识啊。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不存在单独生活的个体。每个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家庭、邻里、社区以及更大的共同体之中。
比如你一出生,首先知道我是爸爸妈妈的孩子,知道自己是隔壁小红的邻居,知道自己是学校里哪个班级的成员。可能要到十几岁才会想到,我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对每个人来说,群体当然是在个体之前就存在的,个人也总是在社会关系中成长的。所以社群主义的观点似乎才更符合现实,明明是社会构成了个人,而不是个人形成了社会。
那么,个人主义这种观念怎么会出现呢?不仅出现了,而且还形成一种思想传统,到了现代社会,不只是思想家这么想,普通人也会觉得个人是第一位的,是最基本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你想,如果这种个人观念根本就是虚构的,却还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基础。那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沙滩上,随时都可能轰然倒塌!
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困惑不解。直到1994年,我读到了沃尔泽的那篇文章,才一下子豁然开朗。
原子化的个人与高度流动的社会
文章的开篇指出,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个人观是虚构的,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但又批评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造成一个对公共事务冷漠、人人自我中心的社会。
但沃尔泽犀利地指出,这两个批评是相互矛盾的,你不能批评这种原子化的个人是虚构的,又批评这种虚构的个人实际上造成了有害的影响。这就好像是说,一个故事里虚构的小偷,结果在现实中真地偷走了你的钱包。
那么,沃尔泽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认为,个人确实是被社会塑造的,社群主义的这个观点没有错,但社群主义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正是这种新型的社会,才造就了自由主义的那种“孤立的个体”。
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流动性” ,总是在不停地移动和变化。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 地理上的流动 ,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和语言文化的障碍。
其次是 社会身份的流动 ,子承父业的传统状况越来越少见了,人们的社会身份很容易变动。
第三是 婚姻的流动性 ,现代的婚姻和婚姻构成的家庭也变得更加不稳定。而家庭是所有人开始进入的第一个社群,家庭不稳定了,自然也会影响新一代人对社群稳定性的认知。
最后是 政治上的流动性 。人们的政治信仰更容易发生变动,更容易改变自己支持的政治派别。
“自愿型的社群”与“后社会的状况”
那么,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
当然有。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做“ 自愿型的社群 ”。 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愿的联合”。 自愿的意思是,如果想要退出,你总是可以退出。 婚姻是自愿的,就意味着你总是可以离婚。
新型的社群也是这样,比如你参加了一个马拉松俱乐部,参加一个公益环保组织,加入了民主党或者共和党,这些都会构成你的社群关系,都会塑造你的身份认同或者归属感,但它们都是你自愿加入的,你也可以自愿地退出。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好吗,既能拥有社群,不再孤立,又没有失去自由和选择的机会。但沃尔泽指出,并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自由是有代价的。
你想啊, 更容易改变的社会关系,就是不稳定的关系。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现代人总是喜欢改变主意,更重要的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高度流动。
比如你很喜欢自己参加的那个马拉松俱乐部,但因为你要搬家了,就不得不退出。如果其他人也有自己的原因放弃了,那俱乐部就只好解散。
沃尔泽把这个高度流动的社会状况,叫做“ 后社会的状况 ”。
我们还能恢复传统的社群吗?
现在,回到开头的那个大问题, 那种孤立的、所谓“原子化的个人”观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这种“后社会状况”塑造出来的。 沃尔泽把这种个人观念叫做“ 后社会的自我 ”。
自由主义者支持这种“后社会的自我”,这让我们可以“自愿地联合”,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但社群主义者却为此悲叹。
那么,能不能恢复传统的社群?让人们重新找回那些稳定的依恋关系、深刻的归属感以及可靠的生活理想呢?
这很难做到。因为你无法限制那些自由:移居自由、社会阶层流动的自由、婚姻自由以及政治认同自由。
所以沃尔泽说,社群主义不可能战胜自由主义。但与此同时,自由社会造成的忧伤、失落和孤独,以及政治冷漠等等后果也会如影随形。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不会消失,它注定会周期性地反复出现。
东西之别还是古今之变
最后,我想和你聊一聊沃尔泽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听过这一讲之后,你就知道并非如此。
其实,所有文明开始都是群体主义的。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是“血肉相连”的。
只有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体会到,这种“血肉相连”只是一个比喻。因为 你总是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会进入新的社群。 但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
毕竟, 人的身体存在是个体的存在,这个物理事实只有在现代才获得了更加重要的文化意义。 在现代社会,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才更容易讲通关于你自己的故事。这就是现代社会发生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这并不是东西方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
问答
最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理解自己的,你会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吗?欢迎到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故事。
划重点
1、沃尔泽认为,个人确实是被社会塑造的,但它是被不同于传统社群的现代社会塑造的。
2、现代社会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流动性”,主要包括地理、社会身份、婚姻和政治上的流动。
3、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出现了新型的“自愿型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自愿的联合”,你可以自由退出。由于社会的高度流动,这种社群很不稳定。但我们很难恢复传统社群,因为我们无法抛弃那些让社会变得流动的个人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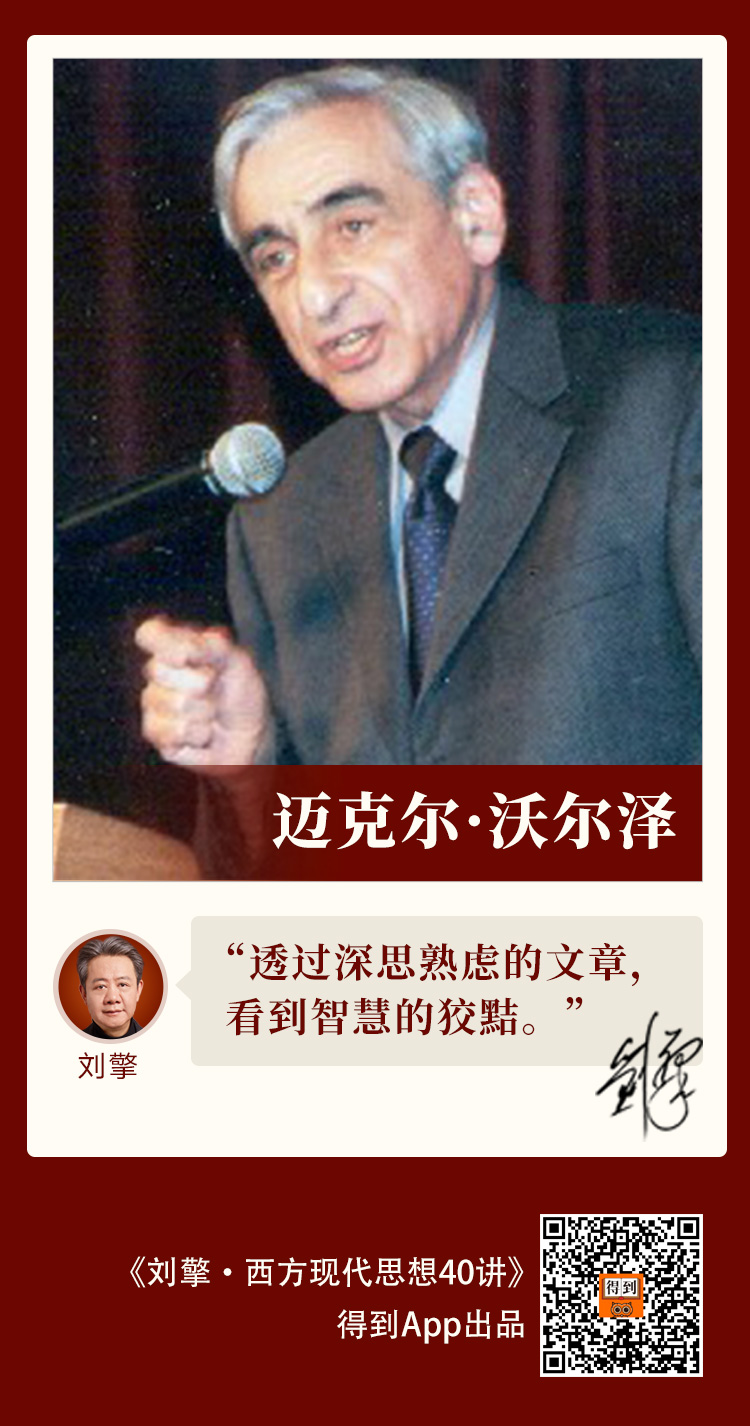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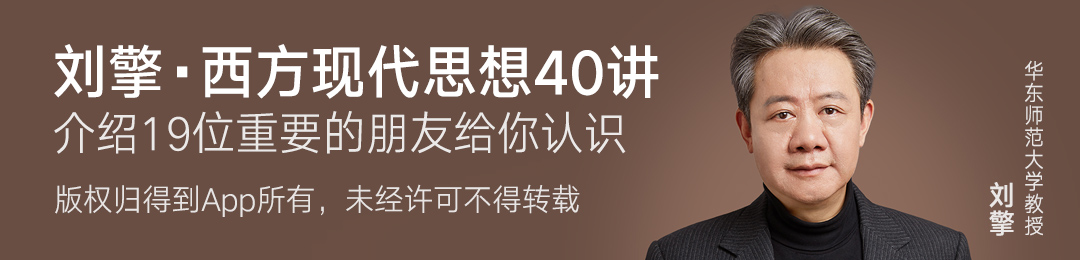
热门留言
廖献平:我是一位74岁的老奶奶了,很喜欢沃尔泽“原子化的个人这一讲”,感谢刘擎老师的课程。我支内退休回上海,回到家乡亲身经历上海的巨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电话,qq email 到如今的微信,个人的颗粒度越来越突显,但同时人们各自信息来源也越来越分散。这时我反而更感觉到自己独立的个体,集体主义只表现在我对自己家庭的责任。微信现在不是我太喜欢的东西了,还有各种自媒体。我越来越想摆脱目前媒介泛滥,反而怀念以前简单唯一信息传递的时代,怀念看书的时代。
佛祖门徒:有一则网上流传的帖子很有意思 :女人认为自己过得很不如意 ,于是她自杀了 。她准备进入天堂的时候 ,一个天使拦住了她 。天使问她 : “你是谁 ? ” “我是玛丽 ·布莱克 。 ” “我没问你的名字 ,我问你是谁 ? ” “我是老师 。 ” “我没问你的职业 ,我问你是谁 ? ” “我是杰克的母亲 。 ” “我没问你是谁的母亲 ,我问你是谁 ? ” “我住在松树街 2 8号 。 ” “我没问你住哪 ,我问你是谁 ? ” … …最后玛丽决定回到人间寻找 “我是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 。 人生而无不在社群之中,如上面这个故事,离开所有社群,很多人甚至无法回答“我是谁”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那么何谈完全独立的个体呢?自我分析是我能够做到人格独立、精神独立、思想独立、经济独立……但并非完全、彻底的独立,如实现经济独立,基本需要在一张价值网或协作网中;如思想独立,但独立的思想往往源自一个甚至几个群体的相互启发和借鉴;人格独立,这份独立的人格往往是在成长历程中被所在的社群不断塑造的,无论我扮演的是服从者还是背叛者。
陈C:沃尔泽的观点给我的启发是,个人主义的诞生源自一种“不适应”,是传统的社群主义在面对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错配”。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如果还是基于社群来认识自身的话,会因为缺乏稳定的归属感而感到不安。从这个角度讲,个人主义的产生是在弥合这种不适应,并在“个人如何自处”的问题上,给个人与社会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回应这种高流动性的社会现实。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这种不适应的源头,会发现它与萨特的“存在就是虚无”有关,与尼采的“上帝死了”有关,甚至还能追溯到一些更远的东西。
意识到个人主义的这种根源以后,我发现自己这几年,其实也在一点一点地经历这种“古今之变”。以前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当前的“归属”,毕竟找到这种归属,会巩固自己所感受到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但过去这些年,我辗转于各处留学、实习,工作后至今也没有成家;虽然也找到了一些新的“社群”,但出于各种原因,对一系列社群关系的归属感却总是比较稀薄的,甚至有时候会感觉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疑惑过,该如何看待自己与社群,又该以何种姿态来生活,随后也就逐渐地接纳了原子化的个人观念,并开始尝试以此为基础做出选择。
Edmund: 我是一个“共同体内在于自己”的“独立个体”。(不知道怎么表达了😅)认为个体自主性的实现可以完全脱离社会框架,是一种自我欺骗式的放逐。个体之“自我”不可能无中生有,凭空创造,我们对于自我的思考不可能逃脱社会给定的框架和舞台,即使这个框架是可以慢慢变动的。
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独白的我。唯独我们内心真正体察到这一点,通往个体自由的旅程才真正开始。
我想只要严肃思考和讨论,“社群主义”与和我们之前谈到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立的,相得益彰。
兔兔 核安全运营顾问EDF:035 沃尔泽|社群|社会善|复合平等
沃尔泽的自愿性社群理论让我有些小惊喜,因为不赞成桑德尔过于强调社群对个人的意义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现代社会的高颗粒度让每个人与社群联系的自主性极高,社群对于个人不具有强制力而是个人选择自己认同的社群。没想到和沃尔泽的观念一样哈哈😄。
老师花了大篇幅介绍了沃尔泽解释的原子化个人是来自于现代化的高流动性的社会,却没有从自愿社群出发介绍他最重要的复合平等理念,有点意外,这是我觉得他最有原创性可以和罗尔斯分庭抗礼的理论。
相较桑德尔的过于强调社群的目的和意义,罗尔斯过于强调个人行动者(原子化的个人动机),沃尔泽不是给出一个资源的分配方式,而是 “围绕社会善本身的意义和内涵来探讨正义原则,并以此捍卫社群主义的政治主张。他所提出的复合平等的主张也因此可以被看作一种以善为中心的分配方案..... 由于不同的社会善总是拥有不同的社会意义,所以对它们的分配最后会形成许多各自独立的分配领域——不同的社会善往往应该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遵循不同的程序、通过不同的机构来进行分配。........ 我们应该支持一种复合平等的主张,在允许少部分人占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定社会善的同时,通过限定不同社会善之间的转换界限,确保所有社会善都能依据自己独特的社会意义,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则和程序进行独立自主的分配。为此,沃尔泽提出了一条永无定论的正义原则:“任何一种社会的善X都不能被这样分配,拥有社会善Y的人不能仅仅因为他拥有Y而不顾X的社会意义占有X。”并且指出,自由交易、应得和按需分配这三种分配方式都可以在复合平等的正义观中得到实现,只是它们都只在自己适用的范围内有效,不能跨越所有社会善的分配领域。” 正义因此归根结底“植根于人们对地位、荣誉、工作以及所有构成一种共同生活方式的东西的不同理解。对这些不同理解的践踏往往是不正义的” - 《西方政治哲学史》
思考题:我确实首先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在海外工作多年的华人,我可能最多认可的就是海外华人这个标签了。从小到大的学校的小伙伴的换了一批又一批,最后能保持联系的都屈指可数了,现在生活中多是工作上有关联的朋友,兴趣爱好小组,都是非常松散的自愿的社群或团体,真的是没有什么共同的纲领性的高认同度的社群了。还是觉得有遗憾的,原子化个人在获得了更多的自由选择的同时也失去了强联系社群赋予的高度意义感。
刘擎(作者) 回复:谢谢你的补充^-^(来自编辑)
欣瞳:也许我们穷其一生都在追求我是谁,努力想给“我”一个更为恰当的名字和归属!人的最大属性是社会属性,所以我认为无论是社群主义还是个人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变化才生出两种派别的存在,这两种思想的存在都有滋生的土壤。
paul leu:在刘老师这两讲启发下,我再次思考两个问题:集体和个人责任,和个人到底是什麽?
道歉是表示悔过。不是你做的事,你悔过甚麽呢?为别人道歉,其实是表示自己和此人分界,并且强调自己不是那类「坏人」。政府道歉是否定以前的政府,声明当局政府不认同那时政府的行为,甚至愿意补偿。二战后的德国政府,日本政府,等,道歉是有意义的。意思是:我门没能防止前任政府做出那些不道德的事,很遗憾。可是七十年后再道歉意义就不大了。除非相信鬼神,不然道歉对象都不明确(扭曲历史事实是另一问题,不可混在一起)。
在完全不同历史环境里,一个当时不在场的政府向另一个当时不在场的政府道歉,有意义吗?或许有:意义就是我们承认那时政府不好,表态我们如今不会允许那种行为再次出现。
但这种道歉隔代越多就越没意义。你为父亲道歉或许还说得过去,但要为上几代祖先道歉就荒谬了。反过来说,对方后代也没有资格接受这样的道歉。接受就表示对方欠你,该以道歉或别的方式赔偿。这种思维导致了某些社会中不文明的代代复仇风俗。道歉,赔偿,欠债,复仇,都是相连概念。
所以我认同澳大利亚总理不道歉态度。义大利难道要向罗马帝国欺负过的人道歉吗?但不道歉并不等于不赔偿。一个国家政府可说是一个超时空的体系。它应该从宏观角度以最佳方式平衡人民利益。这样看,补偿某一部分人是为了超时空的民众利益,该不该补偿和补偿方式都在当前利益而不在祖先道德层面上。
原子化的个体,这节课讲解精彩。不过就连沃尔泽都似乎不全面考虑到个人进化。武志红老师课上每天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是成为你自己」。过去社会对个人进化约制很大,所以只有开悟的人才有可能闯出,极大多数人都停留在集体层次上。「成为你自己」的概念生在蒙田,笛卡尔时代,但直到近六七十年通过心理学进展才逐渐成熟。而成为自己前提是脱离原生家庭。在这个演变下,群体不单单是凭个人兴趣和性格组成,它也是根据个人境界的一个内心组合。「自己」必须突破原生家庭和社会才能达到内心独立和成长,在这基础上便可进化向更宽宏而深刻的集体感。
以往哲学家不重视个人心理发展,容易把个人看成一个定型单位。近百年不但社会变得更複杂,个人也变得更複杂,问题也就越来越有趣了!
左星星:我觉得,现在社会高度“流动性”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驱动力以及由此导致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改变了个人的思想,也就是老师说的,古今之变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随着个人发展的不同,在个人的不同生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加入不同的自愿型社群,并且此后动态的调整自己的自愿型社群 比如,我从小生活的小城市里,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我的小伙伴们都是固定的社群中固定的家庭,大家有着相似的背景和价值观,高考改变了彼此的命运,我从小城市到了一个一线城市读大学,此后大学毕业继续在一线城市工作,我的大多数小伙伴还是继续留在小城市中,就读当地的学校或者做点小生意,虽然我们此后逢年过节也有联系,但逐渐的我发现,我和小时候的小伙伴们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我在逐渐的退出他们已经形成的社群 这个社群的主要话题就是各种家长里短的琐事,闲暇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打麻将,和八卦各种路边社的消息,我对此并不感兴趣,觉得和自己的生活太遥远了,大家逐渐渐行渐远,到不再联系,我完全退出这个社群,这是我自愿的,或者说是大家不同的成长经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同时,我在逐渐的加入新的社群,我喜欢长跑,于是加入了马拉松社群,讨论各种跑马心得,大家彼此激励,世界那么大,我喜欢到处去看看,于是在知名的旅行论坛上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并且相约一起东京巴黎土耳其 随着我个人职业的发展,我认识了很多从事金融财务领域的小伙伴,大家平时经常会对国际时局,金融秩序,股市涨跌,宏观大势等发表各种看法,参与讨论,我又加入了这个社群 有一天,突然有人给我推荐了得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参与了很多得到的活动,认识了不少新的朋友,我又自愿的加入了基于得到,基于终身学习的共同理念,自发形成的新社群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随着自己的发展,不断的离开旧的自愿型社群,加入新的自愿型社群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背后是我自己的自我激励self-driven,以及科学技术的赋能(互联网带来了得到APP) 同时我也想到了邓巴数,随着个人的不断发展,在超过150人的上限之后,就必然要从150人中剔除掉一些人,同时加入一些人,这或许是从数学层面上解释了自愿型社群不断发展的过程吧
王黎璐:我“觉得”我会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跟“别人家的孩子”相比,我很快认识到了个体之间的是有差别,并且差别巨大的。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们应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了机器的正常运作,而甘做里面最不起眼的部件,可也一直觉得,假如我们大家都去做螺丝钉,都去做机器的部件,那么谁来设计、创造、改进这个机器呢?只有独立的个体,才拥有这样的能力。我理解沃尔泽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社群主义是他试图协调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结果。他对待平等的方式,使他看起来像是一位社群主义者,这种方式来源于激进民主传统和他特殊的方法论,即建立在“生活体验”基础上的一种情境化方法。这种传统和方法,也促使他将民主程序视为高于实质结果、现实生活高于哲学职业以及真实对话高于理想对话。
用户51278947:刘老师,你的课讲的特别的好。收益很多。 但是对于个人主义的产生,我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集体主义或者社群主义跟现代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是古今之别而非东西之别,这一点我是认同的。 这种古今转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思想领域,而是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古代生活和生产的方式的特点,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存关系。 这种依存关系可能是存在于血缘的,也可能是存在于地域、社群的,甚至国族之内的。 表现在作为个体要为群体的命运承担共同的责任。 极端的方式体现在连坐制度,灭族或者灭国。
现代社会的特点在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间接性。这种间接性来对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来自于市场经济,第二来自城市公共服务的发展。
城市化和市场经济,使个体可以离开群体而独立生存,与他人的关系是通过漫长的中介完成的。
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是与不特定的,不知名的他人之间的关系。 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事实上存在,却又是模糊的。
不需要知道送快递的小哥的名字,也无需和他建立情感关系,我们也不知道帮我灭火的消防队员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陌生人的关系完成以前熟与熟人之间的合作 。 这种合作是通过复杂的的城市系统和漫长的市场经济链条完成的,与以前的肩并肩手拉手的合作截然不同。
糖小猪:我觉得人很难作为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虽然我门可以强调个性化,但是人总是要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当然,现代社会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包括地理位置,社会身份,婚姻自由,政治立场,看起来可以选择自由流动,但实际上每一次自由选择的背后,都有各种限制的不自由。
伪装:最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理解自己的,你会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吗?
武志红老师新开的心理学课程《自我的诞生》,感觉与今天这一节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 我对自己的理解,从小到大,不管是自己的认知,还是周围人的评价,都是你是从属于某个集体,我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别人也不这么看。 来到得到学习之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想要知道自己是谁,也就是个什么样的独立的个体,导致我甚至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些下意识的隔阂。 到现在,我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或许过去已经为我做出了限制,我还是集体主义的属性更多一些,但是我很愿意自己的孩子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的孩子,别人的朋友,哪个学校的学生。 最后感谢一下老师能开这一门课程,给我解开了许多思想上的谜团和茫然。
肥老太婆:XS35 沃尔泽在批判自由主义虚构的个人观与实践时,也敏锐地反观自己的逻辑。他从真实的世界里发现了自愿型社群的形成、壮大与发展与根源-无论地域、社会身份、婚姻还是政治信仰等方面的高度流动性,其实也为自由主义找到了真实的基石,当然,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是巩固了批判对象后,再有的放矢。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类的天性想享受自由,而现实与情感又离不开社群,如今的网络世界为这两种需求同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调和,但几百万年基因里对真实情感与物理接触的极度渴望,还是会让网络住民不断回归现实世界,融入真实的社群。
刚哥:我有点奇怪,社群是由个人构成,非要把他们对立起来分成两种主义,他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无论在思想和现实中都允许两种“主义”存在不可么。(动辄就贴上主义的标签,实在是令人不爽,给人一种极端化的感觉)
刘擎(作者) 回复:你好,我是这门课的编辑。不喜欢这个词的话,理解成“主张”如何?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不矛盾啊,电影里虚构的小偷线下的粉丝,学着小偷的手法,偷了你的钱包,有什么不可以呢
刘擎(作者) 回复:你好,我是这门课的编辑。哈哈你说的有道理,小偷的比喻确实有点misleading,也许换一个说法吧:社群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水,水这种东西是虚构出来的,但同时又批评洪水泛滥的现象,沃尔泽认为,这样的两条批评是矛盾的,两条批评不可能同时成立。不过,这里的比喻终究是为了方便的理解,这个新的比喻也可能催生出新的误解,最安全的做法,也许还是去看看沃尔泽那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吧。如果能让你产生这样的兴趣,那这节课也算是多少实现了一些自己的价值:)
陈雅文:刘老师,我觉得您这几节课和隔壁武老师的课之间遥相呼应,武老师在引领我形成强大的“自我”,您在告诉我如何在这个社会中安放我的“自我”,以及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感谢🙏🙏🙏 回答您的问题,我首先绝对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这个个体因为这个时代赋予的自由,我才有机会去认识这个广阔的宇宙!只是倒退40年,想想我的妈妈,在农村的她只能在合适的年龄嫁人,养育孩子,哪里有其他选项呢?所以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了我们很多选择的机会。 同时高度的流动性也让人越来越没有归属感,仿佛一切都在变。可我认为人们期待的稳定的依恋关系,深刻归属感,可靠的理想生活,本来是就是你这个个体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拥有了强大的“自我”,是不需要必须有个群体承载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太多人没有这种意识,得到任重道远啊! 回不去的是“故乡”,可“故乡”已经在我心中!🙏🙏🙏
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兴起,源于古今之变而非中外之变!前两天的困惑今天终于解开了!
让我想起得到其他课程中讲述英国脱颖而出的原因是更早的出现了大规模脱离土地自由迁徙的群体。一个好的道理往往跨过学科仍然能逻辑自洽。今天的课程太精彩了!
来回答一下老师今天的问题: 我处在经由社群主义去往个人主义的道路之上的一种状态。我出生在农村,个性敏感,恰恰自己的父亲又得不到同族人的尊重。所以内心一直要脱离原来的宗族群体,起初脱离的原因是证明自己很行,再后来发现证明的必要都没有了,外面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再后来听了得到,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在我一次又一次突破原来自己的过程中,内心慢慢的自由舒展,自内向外的宁静,让我越来越免受外部关系对我的困扰,也不在担心是不同意见者,我大概离自由主义越来越近了。 期望自己能实现罗胖说的优盘人生,不依赖于任何平台而独立存在,但又不拒绝任何有趣的合作。做个有趣而独立思考的人。
你先走:沃尔泽说得很有道理,现代社会流动性太强了,个人主义兴起,一单打开就合不上了。 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群体的力量也很强。是的,我们能自由进群退群,但凡是路过皆有痕迹,有些性质的群自由进出,可能没人计较,但像换国籍、换性别之类的,别人一定会把你和“原生群成员”区别对待。更麻烦的是,我们有些“群”是退不了的,比如时代、基因、文化,所以,我们更可能一直在群体与个体的中间地带游走。
九把叉 方明:社群塑造了个体,个体也可以塑造社群。随着现代社会通讯方式越来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越来越丰富,网络节点直接的连接和重组越来越方便。这种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网络,孕育了更多新的社群,这些新的社群又在塑造新的个体。 一个人是通过周边环境对自己的反馈,而找到自我的,就像蝙蝠在黑暗中通过反射波寻找自己的定位一样。 所以我觉得,离开了社群,个体也就变得很难依存。“我”不是一个绝对的独立存在,“我”是由我最为依存的那些社群所“标注”的存在。
BEING: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随着自己的成长:搬家、转学、住校、换班、升学、社团、兼职……几乎把我和我在的社群全部分开过,一开始是茫然,后来意识到自己总在不停的聚散,就有意收敛了自己的情感,大学期间都是以“以后会分开”的心情在相处,自然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也多了几分平淡。说是分开,感觉其实也就是距离不一样,现在还是会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不过没那么紧密,距离再远一点的社群,基本上就没什么联系了,又有新的社群打理。 人总是不断成长,加入一个社群再离开,有的留恋,有的轻松,有的无谓,因为我们最后都会明白,能陪自己自始至终的,也只有自己。或者这就是现在的人才一直不断的追寻的原因?寻找一个永恒的心灵归宿,最后找到了自己。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