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路标:后冷战时代会有怎样的世界秩序?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来和我一起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我们的课程进入了最后一个板块,开始讨论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
什么叫后冷战时代?1991年,苏联解体了,冷战当然也就结束了。 后冷战时代,就是从1991年至今的时代。我们还处在这个时代,它的重要特征就是还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办法盖棺定论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来为这个新的时代命名,就加上一个“后”字做前缀,叫“后”冷战时代。
那么,怎么理解我们正在其中的这个时代呢?这是所有人都面临的新问题,也是这个课程板块的主题。
在这一板块出场的思想人物只有两位,就是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肯定会有人质疑,为什么只选他们两位?在当代那么多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当中,难道他们的水平最高,观点最正确吗?
学术水准高低,观点是否正确,当然是可以争论的。但 在我看来,福山和亨廷顿两位学者,有一种难以争议的重要性。因为在后冷战时代,他们是西方思想辩论的议程设定者。什么议程呢?就是针对“如何理解全球秩序”这个大问题,各自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式。
说来很有意思,亨廷顿和福山是一对师生,但他们的理论模式是相互冲突的,对应着后冷战时代的两种世界趋势。什么趋势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故事说起。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1997年的8月31日,西方许多媒体都报道了一个大新闻,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你可能知道,那一天,戴安娜王妃因为车祸在巴黎去世。
这可能是一条令人悲伤的消息,但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巴格沃蒂教授却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另外的东西。他说,戴安娜之死就是“全球化的缩影”。
何以如此呢?他是这么解释的:
“一位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一个法国的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她治疗的是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是从一台电脑上读到了这个消息,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制造的芯片,韩国生产的显示器,在新加坡组装,运到硅谷,最后由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送货给你……我的朋友,这就是全球化。”
是的, 随着冷战的结束,曾经分裂的世界开始融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这正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 它不只是一种宏观的趋势,而且广泛地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细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与遥远的异国他乡的生活,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但在另一面,关系越紧密,也就越容易出现摩擦。随着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被拉得越来越近,一些原本容易彼此包容、或者至少可以漠不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甚至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冲突。比如,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就是一个例子。
你看, 与全球化浪潮一同到来的,还有反全球化的浪潮。
我们最初看到的反全球化力量,往往是来自国际秩序中的一些弱势国家,它们希望抵御来自西方的冲击。但到了近几年,我们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强劲的反全球化势力,包括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体现为排外、反移民和脱欧等等现象。
当我们把视角拉开,俯瞰这个世界,就会发现两种相互抵触的大趋势:一个是 全球化 ,世界走向相互融合和依赖,强调人类的共同性;而另一个趋势是在抗拒这种全球化,可以叫做“ 逆全球化 ”,也有学者称之为“部落化”。
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对应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两种现实趋势,福山提出了“ 历史终结论 ”,而亨廷顿则提出了“ 文明冲突论 ”,这两种理论甚至在格式上都很像。我曾开玩笑说,这对师生好像是给大家上了一幅对联。
福山先写了上联,他在1989年发表了文章《历史的终结?》,标题末尾打了个问号。三年之后,他去掉这个问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
亨廷顿对了下联,他在1993年发表了文章《文明的冲突?》,标题末尾也有一个问号,三年之后也去掉这个问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是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
你看这对师生,学生福山写了上联,老师亨廷顿对了下联。但其实亨廷顿是在批评福山。他1993年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福山的名字,但文章第一句就提到了历史终结论,整个文章的意思就是,不同意。
两位“预言家”
为什么他们提出的两种理论会引起热烈的讨论呢?他们之间的分歧又究竟何在呢?这需要回到历史情景中才能理解。
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是在冷战的末期。他的观点,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是最好的制度选项,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就抵达了终点,在这之后不管发生什么,意识形态的竞争已经结束。他的文章发表两年之后,苏联解体了,西方赢得了冷战,福山被看成像是先知般的人物,“历史终结论”成为了这种胜利的理论解释。
但不到十年,就发生了911事件,这几乎像是当头一棒。西方思想界开始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于是,“文明冲突论”就走到了台前。
文明冲突论的要点是什么?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世界上有七种(或者八种)主要的文明类型,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在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之后,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会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态。文明冲突论最早发表在1993年,911事件发生后,也被看作是预言了历史。
你看,福山和亨廷顿,一个说历史终结了;一个说并没有终结,还有文明的冲突呢。师生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那不吵起来才奇怪呢。但仅仅这么看,只是看到了他们的分歧的最表层。
“制度”与“文化”之争
他们之间更深层的争论焦点在哪里呢?其实,这是“制度”与“文化”之争。就是,制度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文化?究竟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会改变文化?
福山认为,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是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文化。只是因为首先在西方出现,就被人看成是西方的制度。是否选择这种制度,虽然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文化并不是决定性的。福山认为,在本质上,这种制度是现代化的结果,而现代化是全人类发展的普遍逻辑。
这就好像是,咖啡树这种植物最早出现在非洲,但在根本上,种植咖啡树需要的只是一定的光照、热量和水分条件。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在美洲和亚洲都可以种植咖啡树、生产咖啡。如今,咖啡已经成了全球性的饮料,你一定要说咖啡是一种“非洲饮料”,那听上去才奇怪呢。
当然,文化也会对制度产生影响,但福山强调,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也可以转变文化,转变的过程可能很慢、很曲折,但人类终究会在制度上越来越像,同时也可以保留自己文化的特殊性。福山本人是日裔美国人,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既有最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又很好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但亨廷顿不同意,他认为,福山低估了制度对于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依赖。亨廷顿认为,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都是高度依赖于西方文明;尤其是民主政治,他认为这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产物。所以,非西方文明很难接受西方文明的制度,日本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外罢了。
那么,如果制度是特定文化的产物,那么就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文化;但如果制度本身可以塑造和改变文化,那么即使文化传统不同,也可以采用大致相似的现代制度。
亨廷顿与福山的争论,导致师生二人相互疏远了很久。直到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才与弟子和解。感情和解了,但他们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
“正在进行时”的问题
不同文化之间会在制度选择上越来越相似吗?还是必然会形成对抗、甚至走向冲突呢?这是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正在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此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确切答案。
但我们应该去了解,观点不同的思想家,是如何观察、解释和论述这个问题的,然后,展开你自己的思考。下一讲,我们就先来看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究竟说了些什么。
问答
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前面讲到经济学家用“戴安娜王妃之死”来解释全球化,像这样,在具体事件中,折射出全球化大趋势,你能想到类似的例子吗?想听听你怎么说。
划重点
1、后冷战时代就是从1991年至今的时代,它的重要特征就是还在“进行之中”,没有办法盖棺定论。
2、福山和亨廷顿为后冷战时代的思想辩论设定了议程,对于“如何理解全球秩序”,他们各自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式。
3、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更深层的争论焦点是“制度”与“文化”之争。就是要问,制度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文化?究竟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会改变文化?这个问题仍然在进行之中,还没有最终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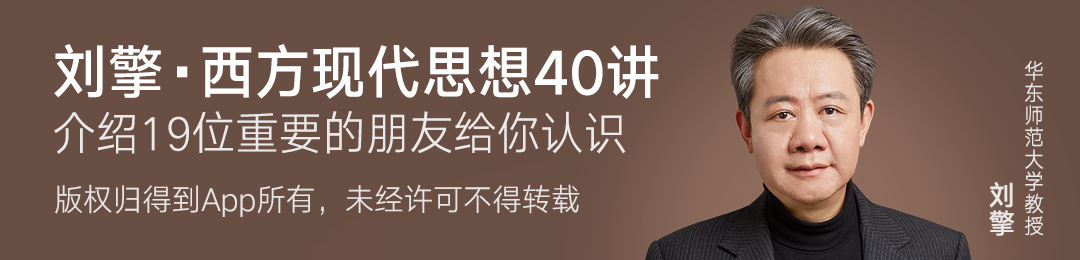
热门留言
陈C:去年听了包刚升老师的政治学通识课,颇受触动。课程里非常多的例子表明,看上去非常美好的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却行不通或者走了样,有些国家反而因制度的改造陷入混乱。而即便是看发达国家的制度细节,也是饱含各种差异,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从那时候起,我有时就会忍不住去想,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一种特定的制度又需要何种条件,才能在一国之中确立起来。
这个问题细想想会非常复杂,但至少在我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肯定有问题的。如果还是用咖啡来打比方的话,尽管种植咖啡只是一定程度的光照、热量和水分的事,可问题在于,咖啡需要的光照、降水、温度等条件,不是每个地区都具备的,一些地方就是种不出咖啡(或者代价过于高昂)。
如果还要再进一步的话,各地的咖啡还存在风味的差异。甚至收获咖啡还只是最开始的一步,后面烘焙到什么程度,又要用何种方式萃取、要不要加配料,都会极大地影响实际喝到的“饮料”的口味——这就如同一种制度在各个国家会以不同的姿态落地,而后续的落实又需要一系列的,且在不同国家间呈现出多样性的,各类配套法律与制度来保障。这就使得即便杯子里都是名为“咖啡”的制度,其实也是产自不同地区,用不同方法加工而成的,口味迥异的“饮料”。
从这个角度讲,制度可能的确会对文化起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是“塑造”的作用。但首先,制度的“落地”需要文化的土壤;而我的想法是,重要的不是文化整体上是什么,而是文化中是否具备制度落地所需要的某些关键要素。在这之后,制度的执行与完善,更会受到当地文化、既有秩序、经济水平等各种要素的影响。
淸风徐来:像我家孩子的成长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
生活上,拿的是囯产的苹果手机,穿的是国产的耐克阿迪等品牌服装,开的是中外合资的汽车。喜欢喝可口可乐,喜欢家乡的面食,也很喜欢麦当劳肯德基。
教育上,从小学中学接受的是中式教育,却一直学着外语。大学上的是中外合作大学,还有两年多的国外留学经历,有着一定的国际视野。
生在中国传统家庭,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却从小伴着猫和老鼠这些动画片长大,喜欢西游记,也喜欢安徒生童话,现在又特别喜欢追韩剧和国际大片。从思想和行为上,已经变成一个活妥妥的混血儿。
王黎璐: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写过一支铅笔的著名故事:制造一支铅笔,从原材料来看,其木质可能来自于美国,笔芯可能来自南美,橡皮头可能来自马来西亚等等,只有全世界分工协作,把各地的优势资源运用起来,以最高的效率去生产,才能让一支铅笔的价格降到几毛人民币。全球化,令整个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是一个后现代问题,并不因为落后而产生的危机;它是一个后地缘战略问题,不能依靠彼此切割,而要依靠彼此合作;它是一个后竞争性问题,不是谁能够率先占领优势,而是如何变成共同解决方案。
Edmund:全球化其实一直在深度进行着,我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孩子们的培训课程表中呈现的本地课程和更具国际化视野的课程,比如国学诵读、人工智能、苹果编程语言…等等,这都是浮在表面的的全球化,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大工业生产的物件,我们如果深究起来,其背后的设计理念、传达的思想、倡导的生活方式、以及物理构建都是全球化的。
有段时间,受新闻影响,觉得在贸易、国际政治、全球治理等领域,我们不可置疑的走向逆全球化了,直到看到隔壁《邵恒头条》有一期所举的例子,很好的回答了我心里的疑问,全球化表现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海平面以下,它以一种更加高效和聚合的方式一直在深度进行着。
以下是引用:
“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因为中国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不少跨国公司都在把供应链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不过,去年路透社对苹果的供应商做过一个量化分析。他们统计了过去5年苹果公布过的200多个主要供应商、750多个生产地点。结果发现,从2015年到2019年,苹果跟中国制造业的结合其实一直都在深化。
2015年,苹果44%的供应商工厂在中国,到了2019年上升到了47.6%。光是富士康一家,在中国的生产地点就在4年之内从19个增加到了29个。而另一家供应商和硕联合,在中国的生产点从8个增加到了12个。
类似的,对于亚马逊来说,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也是与日俱增。 去年,一家市场调研公司研究了亚马逊网站上最火的10000个零售商,结果发现中国的零售商占比达到了38%,两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5%。
其实,供应链的确有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低端产业。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更高端的产业在中国的根却扎得更深了。”
许晓萌:我之所以认为集权是贬义词,是因为在网上混的这十多年,无论是贴吧,还是微博,还是公众号,或是以前的各种论坛以及qq群,我见到的网民一提到集权,想到的就是中国,朝鲜等国家,然后就演变成对政治体制的抨击和谩骂。可能是样本不够大,但我有一个感受是,老百姓和学术圈对一些事情的定义以及对事情的评判不一样。虽然可能大部分时候老百姓不对,老百姓的认知也难以集结成册更难以流传久远(时间上),但在“尘世中”,老百姓的认知无疑在有些时候比学者的认知影响更广,可能影响也更大。因此我才会认为集权是贬义词吧~
刘擎(作者) 回复: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猜公共讨论中,“集权”常常被贬义地使用,很可能也与它和“极权”的混淆有关系。语言的流变对沟通的影响确实很大,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展开讨论的时候,往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厘清概念。(来自编辑)
Super Tank:波音飞机的制造,是很好的全球化例子:
它座椅来自德国、部件来自中国,机身由意大利的公司负责,而机翼和尾翼,全部外包给了日本的重工业财团。波音到最后,只负责建造飞机35%的部分,以及完成最后的组装。 曾经的波音CEO甚至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是一个装配公司,或者叫设备集成商。”
结果出了事故,却是关系全世界的大问题。
个人认为,福山和亨廷顿的分歧,没有谁对谁错,全球化的趋势和文明的冲突或也无法阻挡,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深入参与,细心观察,兴许,世界的秩序会因为每一个这样的个体而改变。
以上,请老师指教,谢谢。
金戈铁马:在如今的社会,全球化的大趋势,已经渗透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我自己的公司为例,我们主要是从事环保装备制造领域,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来自以色列的一家科技公司,也就是产品的研发工作,是在以色列完成;而在研发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自己国内的工程师们负责产品的转化工作,也就是将产品原型转化为在工厂生产制造的图纸。而具体到产品所涉及到的设备、材料采购,其中80%以上都是在国内采购,但是其中一部分核心组件是来自英国的厂商,也有一些关键设备是从德国采购,而控制系统的原产地是美国。而近期我们所承接的一单业务,将产品加工、组装完成之后,最终的用户又是在韩国。可以说,在如今的世界,全球化已是时代的大趋势,无论未来逆全球化的浪潮为带来怎样的结果;至少在当下,全球化依然深刻的影响着我们每个人。
鸿涛:华为是一家全球化公司,它的总部被设计成一座欧洲小镇,设计师是日本人。华为的物流中心在墨西哥和罗马尼亚,财务中心在毛里求斯,金融结算中心在荷兰,风控中心在英国。华为在全球建了50多个研究所,沿着当地的科研院所、人力资源去做建设,比如,材料研究所在日本,微波研究所在米兰,等等。今天的华为在全世界雇佣了 700 多名数学家,800 多名物理学家和120 多名化学家。任正非仍不满足,他还希望得到一些脑神经科学家。全球化已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展开,因为这意味着高效率的连接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
斜阳:关于制度与文化哪一个是第一因的争论,就好比说环境和基因哪一个要素对人的性格形成更重要一样,这没有绝对的答案,因为两者本就是协同共创性的,也是互相影响的。
有趣的是,如果继续以基因和环境做类比,引用一段万维钢老师解读《行为》那本书里面的一段话:“你考察的环境越多,就越会发现环境因素重要;你考察的环境越少,就越会发现基因重要”,所以哪个更重要,取决于我们的主观视角,如果一定要区分和更客观地看,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更具体的情境中观察,比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里的孩子,基因的影响就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家庭里的孩子,环境的影响就越大。
我以为,这个思路用在制度和文化的辩论上,也是一样的,对于经济水平高的国家来说,制度更重要,反过来呢,那就是文化更重要。
陈C:像是“戴安娜王妃之死”那般的全球化现象,在各种跨国企业的生产销售中可以说是再常见不过,哪怕只是像我司这样的小企业。
我们公司有一类工程上使用的小型设备,就是这种“国际混搭”的产物: * 设备的关键技术来自荷兰的技术办公室; * 整台设备由瑞士的总公司设计;主要的驱动部件是丹麦品牌,在另一个国家生产; * 框架结构是铸造件,铸件产自瑞士、法国或者意大利,在总公司内用德国生产的机床加工成型; * 主要部件运到国内,再采购其他的配套部件。这些部件可能是用来自南美的铜制成的,也可能是另一个地区产出的铁矿石,经由国内做成钢材,再加工成零部件; * 所有的东西在国内组装好以后卖给客户,客户则会将产品带到非洲或东南亚,参与当地建设。
其实脱开工作,就连我此时听课、写留言用东西也离不开全球化。键盘是国产的,播放课程的小音箱则是美国品牌、越南组装。课程连同印象笔记分屏投在iPad上,iPad则又是一个复杂的全球化产品。此刻我随手拿起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虽然水是国内的,瓶子也是国内生产的,但制作瓶子所需的原材料,却是中东出产的石油。
全球化在不知不觉之间,便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天天天蓝:刘擎老师您好! 早一个月前,美徳州休斯顿市超市及药店没有口罩、没有家用消毒药水。 医生开长期用药处方从三个月的量缩减到两周。 取消所有非应急手术,包括牙齿手术在内。 因为中国的防疫居家隔离政策阻断了全球供应链。美国医疗资源60%依靠中国供给。所有目前储备医药资源全部留给抵制新冠疫情。
如果生活用品还可以紧缩或替代,但医药器械和药品,是当下美国抗疫急需用品。 这一块全球贸易链的连接什么时候能恢复,对全球来说,都是重中之重。 中国加油!
伪装:前面讲到经济学家用“戴安娜王妃之死”来解释全球化,像这样,在具体事件中,折射出全球化大趋势,你能想到类似的例子吗?
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 比如说这一刻拿着手机留言的我,用的是华为的手机,但是里面大量的零部件分别来自于美日韩,而这些零部件的设计可能来自于全球各地。 手机的系统是谷歌的安卓系统,这个系统虽然是在美国研发的,但是研发者几乎汇集了全球的计算机编程人才。 我的手机平时都用4G网络,偶尔也用WiFi,这两种技术大多数都是来源于国外,里面不同的公司拥有不同比例的专利技术占比。 我还有一部小米手机,里面的成分更复杂,制造小米的公司成分也更加复杂,还在香港上了市,世界各地的人都买了他们的股票。。。 如果我更懂的一些手机软硬件知识,可以更加详细的罗列一些信息,但就全球化的分析来说,并没什么必要。
光辉:在具体事件中,折射出全球化大趋势,你能想到类似的例子吗? 1.我只能谈谈现在已经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本人坐标广州,广东政府已于3月28日正式关闭了境外人员来华通道,每周每个航班飞行次数不超过一次。 2.我感觉这次疫情可能开始并不仅仅是在武汉,而仅仅是由于我国政府率先发现并确诊了它,然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有可能其他国家的公民在发病死亡后,也不知道其实自己的死是由新冠引起的。 3.通过这次的疫情蔓延速度之广,涉及范围之深。我们深刻领悟了全球化,地球村,以及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由于通信 交通工具等等一系列的科技进步。遇到灾难,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Tian:我看过一个叫“艺伎回忆录”的电影,就是美国的导演,日本的故事,中国的演员,法国的作曲家。 这算不算全球化?
朱家乐:我认为文化和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是能具有不同的地位的。也就是说,在某些条件下,文化决定制度。但在其它的一些特定场景下,制度又能改变和决定文化。
在没有强制性外来文化力量的干涉下,一个独立的社会是会先产生社群文化,然后再慢慢形成制度的。在这种社会下,文化决定制度。世界上不同文明的最初起源就是这么来的。
但像日本那样的社会,制度却又直接改变了原有文化。这是因为美军驻扎日本,给日本进行了强制性改革。日本社会被胁迫了。在这种压迫性情境下,被压迫的社会在文化完全不认同的情况下,强行颁布了一套和原有文明背道而驰的制度。这种制度虽然不能瞬间就改变文化,但却能细水长流一般的渗透进社会结构,使得文化慢慢地进行全面改变。
因此文化和制度谁更具有主导性是看情况而定的,并不能直接一概而论。
九把叉 方明:我觉得全球化或许是最终的结局,这当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其实全球化的进程一直在发生,从智人走出非洲,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乃至英国炮舰轰击虎门,都是全球化的过程,其中无不伴随着冲突。 全球化的进程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速度正在加快。 但是,还要看到一个现象:在互联网上,正在形成新的圈层和文化,而且彼此隔绝。那会不会在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同时,在互联网上形成新的割裂呢?
陈雅文:刘老师,我是做医疗行业的,我们做手术用的设备是荷兰产的,整套手术耗材器械来自分别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最重要的是,能使用这些产品的已经不是某些人或阶层,他(她)可能是某个乡村里普通的大爷大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全球化最好的折射!🙏
兔兔 核安全运营顾问EDF:38 路标|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秩序 没有按顺序,直接跳来学最后一模块。
早几年看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改变了我对世界政治格局的认知,后来听到了对他的批评,比如过分强调文明对政体的影响,又开始疑惑。
最近开始看福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看到他其实对自己早年提出的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做出了相当的修正,比如他强调了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的建构(动员力),法制,和责任制政府。各国建国的历史路径不同,导致了这三个要素的状态不同,西方因基督教传统先建立了高于王权的社会秩序,后来才能演化出制约王权的法制,最终经历社会变迁各个新兴阶层被纳入政治力量,发展出今天的代议制民主。
在如何到达丹麦(良好政治秩序的国家)这个问题上,看得出他虽然没有改变结论,但是做了很多努力去完善这个理论的。略读该书的结论篇,感觉他也还是没有回答是不是所有国家都最终必须要到达丹麦这个他自己的问题。他的老师的理论应该还是和他的理论研究发生了化学变化的,着实有趣。
谢谢老师拔高了我对这对师生的思想的认识深度,之前只是简单的觉得两个人针锋相对,一个强调存在普世大同的伦理政治秩序,另一个强调对历史路径的依赖。但其实他们的实际分歧其实也许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福山在最新著作中也探讨了对历史路径的依赖,比如他带着些悲伤的宿命论的口吻,指出没有在国家建立前发展出法制雏形的国家要发展成自由民主政体的困难。不过看亨廷顿最近的谁是美国人一书似乎并没有淡化文明冲突的因素。
也许在遥远的将来这两位的思想和之前的巨匠们比不算什么,但他们俩确实设立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贝达人:用着韩国牌子的手机,听着中华文明的老师讲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的课,想着全球的制度和文化的故事。担心疫情在全球传来传去。 🤔 没有办法不全球化呀。……
独一村:清华大学秦晖老师关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看法,我摘录几点作为这个话题的拓展阅读。 “我反对“文化决定论”,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从认知上讲,只有对拥有同样选择自由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他们到底选择什么并且议论这些选择的好坏。我对在不同制度平台上能否进行“文化”识别,乃至开展“文化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就持怀疑态度。 第二,从价值观讲,我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中餐西餐可以各有所爱,但饮食自由无疑比饮食专制好。基督教与儒家各有千秋,但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当然比异端迫害、神权专制进步。 第三,从因果方面讲,文化与制度并无对应关系,也很难说有什么因果逻辑:不能说吃中餐就会导致饮食专制而吃西餐就会有饮食自由;西方基督教国家今天通行信仰自由,可是当年他们的宗教审判与神权政治也不比今天的一些国家弱。” 这个话题涉及到历史能不能解释,存不存在必然规律? 秦晖老师怀疑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观,认为历史因果链只在短时段有意义。 美国思想家悉尼·胡克有句名言: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