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餐11 怎么理解“深刻而片面”的萨特?
你好,欢迎回到西方现代思想课,我是刘擎,这是我们加餐的第十一期。
提醒你一下,在听这一讲加餐之前,你需要学完课程正文的【第14讲】和【第15讲】,才能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内容。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萨特的自由观是否太过绝对和苛求?
先来回答学友“树上鸽子”的一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
“树上的鸽子”
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我有一个疑问:萨特通过人生而虚无推出了人生而自由,但好像他这样的自由观是否太过于强硬了,我的意思是他对于人的自由性是否近乎于绝对和苛求,在这种强力要求下,那些阻碍人实现自由的条件和枷锁好像总是能超越的,但现实生活中其实挺难的。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有代表性,我最初读萨特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
其实这也是许多人质疑萨特的地方。比如他在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写《辨证理性批判》时就说,工人阶级没有自由,在社会制度根本转变之前谈不上自由选择,诸如此类的话。但萨特又说,“人被判定是自由的”。那么,萨特是不是自相矛盾了呢?
我想,恰当的理解方式是要看到, 萨特的自由概念非常特别,他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来讨论自由,是要揭示人的存在结构,这个结构有一种不是“现成的(given)”而是永远不断要 “造就的”(made) 的特征,这是人的界定性特征,
那么这种自由的概念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谈论的自由,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萨特说的自由,不太联系到实际选择的可能、障碍、种类和资源等等,也不同于我们后面讲的伯林的自由观,因为伯林说的自由主要是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自由(《两种自由的概念》)【点击进入课程第26讲-伯林:你想要的是哪一种“自由”?】。
但萨特的自由与我们的生活又不是没有关联的。更仔细一点说,他认为人其实是包括“自在”和“自为”两个部分,我们的身体是生物性的,基本上是“自在”之物,至少很难随意塑造。但我们的意识是“自为”的部分,是自由的。
比如,有一位身体残障人士,可能会说,我身体有残障,怎么自由呢?萨特会说,对,你的身体残障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因为身体是“自在”的部分。但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残障、做一个怎么样的残障人士,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悲观哀怨的残障者,也可以选择不断超越自己的身体局限性,做一个残障的勇士。残障的勇士是凭空杜撰的吗?当然不是,你可以去看看残奥会,或者,去看丹尼尔·刘易斯主演的传纪电影《我的左脚》(顺便推荐这部我年轻时候深为感动的片子: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1294000/)。
无论如何,萨特的自由选择并不是意味着你有无数选项,或者可以为所欲为。他的意思是: 人的处境永远存在“别的出路”,绝不是“别无选择”。因此,你总是可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选择的结果。你说你不选择,那么这是你选择了“不选择”,不选择也是你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注定的。所以,“别无选择”永远是一个托辞,他对艾希曼的反驳就是如此。
“我们”有可能形成“共同的主体性”吗?
接下来,我再谈一点我个人对萨特的理解和感受。
听到“他人就是地狱”的说法之后,我们会思考:主体之间的合作甚至尊重和友爱是可能吗?萨特是不相信的(而我相信是可能的)。
在萨特看来,面对陌生人的注视(le regard),你和他会为“争夺主体性”而斗争:(在陌生人的“注视”下)你会沦为一个对象、一个“自在”之物,或者用萨特的另一个术语说就是“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面对这种处境,你会反抗——人和人彼此之间只有永恒的斗争。
实践主体性的“自为”存在,也可能瞬间变成一个客体(“为他的存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男子正在偷窥一位女生(这个女生正被他对象化,变成一个物)。但他突然发现背后有人经过,目睹了他的偷窥,顿时羞愧万分,因为此刻他从注视的主体瞬间沦为一个被注视的客体。
个人的主体性必须以他人的对象化为代价吗?有没有可能形成“我们”这样一种共同的主体性呢?在600多页的《存在与虚无》中,只有大概10多页的篇幅,萨特探讨了形成“我们”的可能性,但那是一种消极的“我们”。
比如,你和同伴一起走在街上,对面走过来一个人,注视了你们俩,同时把你们俩都当作客体。这时候你们就会形成一个“我们的”意识,是共同作为对象化的集体意识,萨特称之为“同他的存在”(being-with-others)。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是如此,起源于这种共同受压迫的消极体验。
萨特说,我们会渴望一种理想:就是同时拥有“人的自由”和“人的对象性”。但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幻想。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把自己摆平”,摆得彼此平等,无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也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彼此尊重自由是不可能的。而宽容呢?其实对别人宽容就是“把别人强行抛入一个被宽容的位置”,这也是一种对象化,在原则上不容许他们自由选择。
的确,萨特揭示了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体验,但这类消极体验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相信,我们确实有共同的积极体验,伴侣、友人以及团队,这一切并不是表象,也不都是过眼云烟。这些经验是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值得”的源泉之一。 而这些积极的共同体验,也有哲学家来做理论阐释,称之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会请他出场。【点击进入课程第37讲-哈贝马斯:为什么“交谈”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总之,萨特的思想具有一种“深刻的片面”,我们不要因为他的深刻而陷入一种极端的片面;但也不必因为他的片面而忽视了他深刻的洞见。学习而成为自觉,就是这个意思吧。
萨特的“存在”与海德格尔的“存在”
下面谈谈我自己读萨特的故事。在1987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出版了中译本,销售了20万册!我当时读得昏天黑地,一知半解。第二年,有机会在北京听到译者陈宣良先生的讲课和辅导,大有启发。但我自己更多地是从萨特的戏剧作品中体会他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后来有了更多的学习,特别是对海德格尔的学习,也就明白了萨特在哲学上的局限。 其实海德格尔才是进入了“存在”的世界。而萨特只是着眼于“存在者”(或者“生存者”,人的生存)。 海德格尔是通过此在(生存者)来追问整个存在,而萨特似乎不理会那个更大的——把无数存在者联系起来的、让所有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存在。所以,海德格尔自己从未认同“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这个标签,其实这个词最好译作“生存主义”。
这门课最初的计划中是包括海德格尔的,但他专门的术语太多、理论太深奥,门槛实在太高了,我最后决定放弃了海德格尔。
但是呢,我也曾经有过几次成功的尝试,是给本科生讲海德格尔,达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我只选了一篇海德格尔的文章,在课堂上逐句讲解。孙周兴老师问我,你选的哪一篇?我说就是你翻译的《物》,他说真有眼力。所以,对于学有余力、又对海德格尔感兴趣的同学,我推荐这篇文章《物》,这其实是一篇演讲,收入他的《演讲与论文集》这本书,也可以在网上找到电子文本(https://www.jianshu.com/p/a37403a802c6),你可以搜索一下。
因为有同学提到海德格尔,我就应答一下。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了。
不可替代的萨特
回到对萨特的感受。后来我认为,萨特作为文学家的成就高于哲学家。而且在我进入到专业的政治哲学研究之后,也对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论述有了更多的质疑。在这方面,他曾经的好友和后来的论敌雷蒙·阿隆显得更为清醒。阿隆早就觉察到“知识分子的鸦片”及其毒害。
另外,作为存在主义人生哲学的实践者,萨特的生涯很容易吸引年轻人。但在成年之后,我个人也慢慢疏远了他的风格。在他动人心魄的经历中总会看到一些浮华的表演性,或许有一半是我们不习惯的“法兰西文人气质”吧(这在当代法国的哲学明星Bernard-Henri Lévy身上更为显著)。
1993年Bianca Lamblin发表了《一个被勾引的女孩的回忆》法文版,很快就有了英译本,书名改作A Disgraceful Affair(一段不光彩的情事)。作者回忆了她在17岁的时候被诱惑,卷入了萨特与波伏瓦的生活,经历了一段迷乱复杂的“三重奏”性关系。她的回忆带着受伤害的精神创伤,有些情节让人难以置信。无论作者的记忆是否准确(她还有许多书信作证据),萨特与波伏瓦的故事失去了那种“神仙眷侣”的光环。
萨特和波伏瓦半个世纪的伴侣关系仍然是弥足珍贵的,甚至仍然是legendary(传奇的)。但像所有终身相守的爱情传说一样,当事人也同时是“幸存者”(in many senses)。.
萨特让我有过幻灭的感受吗?never,从来没有过。他的光环是渐渐褪去的,变得更真实,更接近可以想象的人,但仍然是我心目中一个英雄般的存在。
我知道,这里有偏爱的私见。在年轻的时候,在你最渴望生命力的岁月,这个人唤醒了你,启迪了你,激发了你,并且以他的思想为你作证,因而塑造你的青春生命。这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你没有另一种不同的青春,这是你唯一的历史。那就坦白承认好了,毕竟,你没有踏上弗罗斯特说的“The Road Not Taken”(另一条路)。
很多次听到我们这代人中间,有人鄙薄萨特,以此显示自己的成熟高明。我会轻轻一笑的,觉得这种鄙薄才更加让人鄙薄吧。
所以,当我读到萨义德(Edward Said)回忆萨特的文章,会心有戚戚焉。萨义德见到了他曾经的英雄萨特,他失望了,但仍然为萨特的去世而悲痛。那时候我还在写文化专栏,就为此写了篇短文。我把这篇文章附在了文稿最后,有兴趣你可以读一读。
好了,这一次加餐就到这里。最后,如果你有什么感想和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到我的知识城邦留言。这些加餐最初是在知识城邦发布的,我把这一讲加餐的原始链接放在了文稿最后,点击进入原始链接,你还能看到同学们之前的讨论。
我们下次加餐再见!
附录:萨义德回忆萨特
爱德华·萨义德2001年在《伦敦书评》发表的一篇文章,回忆了他与福柯和萨特相遇的经历。文章透露了这三位享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979年1月萨义德在纽约收到一份电报,法国《现代》杂志邀请他赴巴黎出席一个关于中东和平问题的研讨会,电报的落款人是波伏瓦和萨特。他在惶恐之中竟然怀疑这是个玩笑,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如同收到艾略特和沃尔夫的邀请去《日晷》杂志的办公室做客”。他用了两天的时间才确认这份电报的确属实,随即接受了邀请。
萨义德那时已经44岁了,刚刚出版了《东方主义》,并由于积极介入中东政治问题而为人注目。为什么他仍然会为收到这份邀请而惶恐?因为在他心目中“萨特一直是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英雄之一。在我们时代的几乎每一个进步事业中,他的洞见与知性天才都发挥了作用”。
萨义德到达巴黎后,在下榻的宾馆中收到了一个神秘的通知:“由于安全原因,讨论会改在福柯的家中举行”。第二天上午萨义德赶到了福柯的居所,几位与会者已经就座,波伏瓦在谈论她去德黑兰组织示威的计划,却迟迟不见萨特露面。他对波伏瓦的喋喋不休没有好感,而且觉得她虚荣得无以争辩。一个小时左右波伏瓦就离开了。
在福柯的书架上,萨义德发现了自己的著作《开端》,这使他感到高兴。但福柯表示他对这个研讨会无可贡献,一会儿就要去国家图书馆。福柯与萨义德之间的交往一直是友好而亲切的,但他从不愿对萨义德谈论中东政治问题。直到福柯去世之后,萨义德才渐渐明白其中的原委。他从福柯的传记中获知,1967年福柯在突尼斯目睹了反犹太主义的疯狂,便中断了在那里的教学工作返回巴黎。但后来突尼斯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告诉萨义德,福柯的离去是由于当时与一名学生的同性恋关系“败露”,被大学当局驱逐。萨义德不知道哪一个版本的故事更为真确。后来他从德鲁兹那里得知,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福柯因为倾向于支持以色列而与德鲁兹争执,这两位一度最亲密的朋友也渐渐疏远。
萨特终于到场了,被一群助理和翻译簇拥着。使萨义德深为吃惊的不只是萨特的苍老与憔悴,而是他在讨论中几乎一言不发,消极而冷漠。只有他的助理以权威口吻不断插话。萨义德打断了讨论,坚决要求听到萨特自己的发言。最后获得的是萨特事先准备好的两页文稿,其中只有对埃及总统萨达特陈腐而空洞的赞美,而对巴勒斯坦的诉求则不置一词。
萨义德终于明白,自己一直被萨特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中的英雄故事所迷惑,其实萨特始终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萨义德带着对萨特的极度失望回到纽约,这是他们之间仅有的一次会面。
次年,萨特的去世仍然使萨义德深为哀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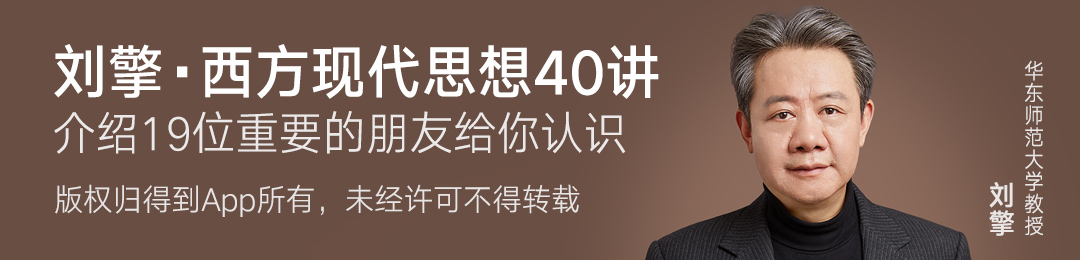
热门留言
淸风徐来: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文章中,对人的自由选择作了更为深刻的诠释。
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当我们说人自己作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作出选择;但是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
我理解萨特的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他所推崇的存在主义的自由,首先肯定了个体自由;二是个体自由的选择包含两个方面,既是在为自己作出选择,同时也是在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三是个体自由选择是有价值的,是要由个体承担相应责任的。
我很欣赏的一点是,“个体的自由选择也是在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听到的一个故事。说是当初人们在交通十字路口设置红绿灯时,做了一个假设,就是每个人过马路时,设想在十字路口周边的楼房窗口里,有许多双儿童的眼睛,在观看着这个人过马路。怎么过马路?是否闯红灯?当然是个体的自由选择。但是这个人,他自己内心若能感觉到,这一行为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在他背后还有那么多双儿童的眼睛在看着他,我相信这个人的自律性一定会在此刻由然而生。
因此说,个体自由选择还是不能过分强调就是自己的事,因为其背后还隐藏着诺大的群体或社会效应。由此可见,个体自由在本质上还应是置于群体之中的自由。萨特把自己所崇尚的存在主义说成是一种人道主义,其思想的伟大而深邃正体现在这里。
王黎璐:我理解“自由选择”实际上是人的自由意志通往相应本质的中介桥梁,选择是绝对的。要实现自我的肯定,决定自己的本质,抗拒荒诞,就要行动,就要干预生活,就要选择。人越处于逆境,就越要自由选择,自由选择机会均等,人人平等。每个人的自由依赖于别人的自由,相互影响和干预,因此这里也涉及到一个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别人就是一种永远威胁着我存在的东西,我的存在就是对别人自由的限制。萨特还认为,人的自由是通过人的选择和行动表现出来的,自由和选择、行动不可分。自由就是选择行为本身,而不是通过选择去获得自由,自由与成功是毫无关系的。自由、选择还有效果的问题,与“责任”紧密相联。人就是自由,人作为一个自由的存在,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事实。 一朵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奋斗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冰心)
金戈铁马:诚然,萨特的理论确实有一种“深刻的片面”;不过,我们每个人对于自由和存在的理解,又何尝不是主观而片面的呢。不可否认,每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时代背景、原生家庭、成长环境、教育程度等等。而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会导致我们对于他人思想的理解方面,不可避免的代入自己的情绪、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看待、评判一种思想观念的时候,往往只是会看到我们想看到的那部分内容;而对于其内涵的理解,也难免会陷入主观和片面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萨特的思想中所存在的片面性,正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很好的警示;它提醒我们,时刻审视自己,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避免陷入主观陷阱。
Edmund:我们可以在萨特和哈贝马斯“主体间性”那里,都能找到共同的主体性的可能,在我看来: 第一、萨特“存在即虚无”分析已经给了我们充分“交往”的自由。
第二、而萨特的“他者即地狱”的分析,恰恰也给“被彼此物化从而才能确定自身主体性”的我们带来“交往”的动力:因为我们要通过“交往”去再次体验、确认和输出自己的“主体性”。而在这种交往过程中,我们真正的新的“主体性”才会被建构出来,即一种共同的主体性。
佘天俊:萨特对于自由,区分为自在的和自主的,这让我想到的是,斯多葛学派和阿德勒的心理学。斯多葛强调不控制你所不能控制的,控制你能控制的,似乎就是萨特的,你无法改变“自在”部分,但你能控制你的“自主”部分。“不选择”是一种自己主动的选择,是阿德勒心理学中让我记忆最深的内容。这算是种强者哲学吧。 偷窥被看到,瞬间从主体沦为客体,这个说法真有意思。沦为客体,就处在一个被判断被评价的地位,从而失去一切控制感。 不过,我还是更认同刘擎老师说的,存在一种积极的共同体验,可以形成我与你的关系,而非一切皆为我与它的关系。就如爱情,友情甚至团队情谊,仿佛是一种独立于所有个体之外,单独存在且有生命的感觉。
我是谁,我要去何方:“萨特的思想具有一种“深刻的片面”,我们不要因为他的深刻而陷入一种极端的片面;但也不必因为他的片面而忽视了他的深刻洞见。”—— 其实,任何知识都具有局限性,也就是有其边界。有时候知识的边界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只有清楚了所学只知识的边界,才能更好得运用,避免生搬硬套。
ZZZZZ1:萨特的“绝对自由”理论,对于渴望更多自由、对传统进行反叛的年轻人是有力的支持
但同时,随着岁月的流逝,认清了真实世界的约束后,我们开始反思萨特“绝对”理论的缺陷
年轻时我们总想改变世界 后来我们努力做到尽量不被世界改变
史努比:不止青春,每一段过往的时光都不可替代、不能重复、无法改写,都记载和见证了,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
尔雅:单纯地理解自由或是限入空荡荡的辩论,或是成为一个人的思想游戏。如果把自由放入关系中去理解,就能认清自由的本质。在哲学中,自由是关于生存与死亡、存成与虚无的暧昧。在经济中,自由是关于富裕与贫穷的配置。在政治中,政治上强制与宽松的撕扯。在社会中,自由是约束与放纵的相互咬合。在文学上,自由是虚拟现现实的紧张。自由是关系中的一种张力,因为关系不断,张力就无限,因此自由主成为永恒的主题。
贾春叶:萨特提到的人的存在结构,不是“现成的(given)”而是永远不断要“造就的”(made)的特征,我非常赞同。这正是我们追求自由的一种必然。在我们的人生之路上,我们需要不断地made自己,定义自己。 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那么人与人之间还可能做到尊重、合作和相互友爱吗?难道只能有“我”,不能有“我们”吗?萨特不相信这一点。但刘擎老师认为这是可能的。对于“他人就是地狱”,我的理解比较狭窄,只是觉得如果把他人的话当成自己行动的指南,可能就会陷入地狱之中。没有从我与他人的关系来思考这件事情。这是需要升级之处。 萨特认为,人的处境永远存在“别的出路”,绝不是“别无选择”。因此,你总是可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看,只要自己存在自由之心,也真的不是“别无选择”,应当还是有别的出路。我个人就是因为有自由之心才获得柳暗花明的新生。因此,身体是自在的,心灵却是可以自为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萨特的自由,的确会让自己跃升到新的、别有洞天的境界。 在年轻的时候,在你最渴望生命力的岁月,这个人唤醒了你,启迪了你,激发了你,并且以他的思想为你作证,因而塑造你的青春生命。谁在我的青葱岁月唤醒了我,启迪了我,激发了我?要想一想,给自己一个结论。 看到刘擎老师说,萨特的文学成就大于哲学成就,就百度了一下他的文学: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恭顺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剧,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迫害,并对反种族歧视的普通人民的觉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剧体现了他主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不过,有机会还要先读一下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这本哲学名著。
雅努斯:生命就是这样,有些人有些话深刻改变了我们,但也只是一段时间,有长有短,因为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话,我们会接着改变。我们没有必要去怪之前的自己轻信于人或错信于话,因为那时的改变才有我当下的反思
BEING:萨特的“自在”和“自为”如果用《活出生命的意义》书里来形容,“自在”就是维克多的身体关在集中营,无法逃脱,“自为”则指他的态度、想法是由自己决定的,是自由的。 萨特并没有像他自己书中表现出来的那么纯粹,且有的思想太片面和极端,但能进行如此深刻的思考,并努力践行存在主义,也是很难得的,令人佩服。
雅努斯:老师,萨特的思想有没有受到佛陀思想的影响,因为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佛教四法印中说诸法无我和有漏皆苦,和萨特的思想很像,诸法无我是说我不是恒常不变的,对应到萨特这就是自在和自为,因为存在先于本质,所以没有我的不变的本质,也就是物我(当然佛教里连物我也视为诸行无常了)。有漏皆苦对应,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欲望永远不会被满足,佛教说人永远在轮回之中(当然佛教中有无记)。佛教肯定修行,也就是行动,相信离苦得乐,萨特也肯定行动,但相对悲观。老师您怎么看?
萝卜特弹:前半段说的内容和《被讨厌的勇气》里面说的“目的论”的思想不谋而合。人永远都有选择的自由,只是很多人选择了眼前的“不幸”。
何小空:请问刘老师 《物》收录在那本书里呀?《物的追问》是一本吗?
刘擎(作者) 回复:刘老师上课用的版本应该是选自孙周兴老师译的《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来自编辑)
活着:自由和自由选择其实不应该是等同的,人生而自由,但是自由选择并不是表示你就可以得到自由。因为前者的自由不必为此付出代价,而后者就必须付出自由选择的代价或者是说后果。
年轻的世界:对这次加餐我理解,萨特的自由说,是指人永远有选择的自由。即便是不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