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餐13 艾希曼究竟是不是“平庸之恶”?
你好,欢迎回到西方现代思想课,我是刘擎,这是我们加餐的第十三期。
提醒你一下,在听这一讲加餐之前,你需要学完课程正文的【第18讲】,才能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内容。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关于“平庸之恶”的争议
阿伦特的思想很广阔也很复杂(她使用的术语,包括“政治”、“权力”、“权威”,“自由”等等概念,都不同寻常),我们只谈了她公共影响最大的一个观点“平庸之恶”。
为写阿伦特的这两讲的讲稿,我用了暑假的整整两个月。在此期间,我重读了阿伦特的大部分作品,还读了许多相关的专业研究,完全是自己一次再学习的过程。但最终,我仍然没有把握。
阿伦特洞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现代政治“病理学”的一个样本,她试图破解这个“病毒”的基因,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多年的思考,她反复不断的尝试,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线索,提出了许多洞见,但它们仍然是暂时的、不完整的,直到阿伦特的临终时刻仍然是如此。我相信,阿伦特自己并没有给出一个彻底清晰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平庸之恶”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在争议之中。
2013年电影《汉娜·阿伦特》上映。我熟悉的一位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里拉教授,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两篇评论,引起了一些争论。我在当年的“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中,介绍了这次争论。我给你读一下当时写下的记录,也推荐你去看这部电影。
摘录:重访《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2013年上映的记录片《汉娜·阿伦特》,由德国著名独立制片人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导演(也是1986年传纪电影《罗莎·卢森堡》的导演),以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风波为主线,在艺术院线获得了相当好的票房,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赞誉,也激发了知识分子重新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激烈争论。
焦点问题仍然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点击进入电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中的判断是正确吗?以所谓“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来把握这名纳粹高级军官的暴行是恰当吗?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纽约书评》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Mark Lilla, “Arendt and Eichmann: The New Truth”,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1, 2013 Issue; “The Defense of a Jewish Collaborato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5, 2013 Issue),评论了多部与纳粹大屠杀相关的电影和书籍。
在《阿伦特与艾希曼:新的真相》一文中,里拉对这部传记片的某些艺术品质予以赞赏,但批评它的情感性叙事基调不适宜大屠杀这样主题,随后指出了影片“最严重的问题”:关于真相。表面上这部电影是关于寻求真相(真理),但它实际的主题并不是忠实于真相本身,而是“忠实于你自己”。
如导演阐释所言,阿伦特是一个“对自己关于世界的独特视野保持忠实的”典范。但里拉认为,这个故事赞颂了一个思想家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勇气,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阿伦特若还健在也会不得不承认”。
里拉的批评很明确:阿伦特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最近十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和文献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罪恶机器上的平凡“齿轮”,或者简单服从、无力思考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和自觉地参与并影响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战略。
艾希曼在1960年被捕之前匿藏于阿根廷,期间他写了长达五百页的回忆录,并接受了一名纳粹同情者的长篇采访(原始的采访录音被挖掘出来,转录文本长达几百页)。艾希曼在大段的独白中骄傲地谈论自己“为了我的血液和我的人民”去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他责备自己“应当做的更多”,并为“总体灭绝的想法未能全部实现”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而“恶之平庸”只是外表和掩饰。
里拉认为,阿伦特写《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本书有两个不同动机,第一是公允地处理所有造成所谓“终极解决”的因素和成分,并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施暴者和牺牲者。在这个主题上阿伦特是一位先驱,当初她受到攻击的许多观点如今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
里拉认为,阿伦特的另一个动机是想要提出一个解释模式,使那场暴行成为可理解的,并使判断成为可能,但阿伦特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她被艾希曼的面具所欺骗,因为她的判断受制于自己思想的先入之见,这些前提源自海德格尔的影响(本真性、匿名的大众、作为机器的社会,以及被现代哲学抛弃的“思”等等),这最终使她的判断走向了一种“过度复杂化的简单化”(overly complicated simplification)。
另一位学者伯科威茨(Roger Berkowitz)是巴德学院(Bard College )的政治学副教授,担任阿伦特研究中心的学术主任。他致书《纽约书评》对里拉的文章提出两点批评(Roger Berkowitz, “Arendt and Eichmann”, reply by Mark Lill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 2013 Issue)。
他指出,首先,里拉像许多人一样误解了“恶之平庸”的概念,阿伦特的要点是将可怕的暴行与艾希曼的无能力(从他人视角)思考相对照,“平庸”指的是艾希曼其人,是他“无言的浅薄”,而不是他犯下的恶。
其次,阿伦特当时已经掌握了部分(大约80页)艾希曼的回忆录与访谈资料,而这些证据支持了她的判断。我们应当摆脱人云亦云的流行误解,重新认真对待阿伦特的论证。
里拉对伯科威茨的批评作出了回应。里拉指出,阐释“恶之平庸”的概念一直是个难题,但阿伦特主要将艾希曼描述为一个“符码”,一个资质平庸(未完成高中学业)的“无目标的人”,认为他“完全没有动机”,也“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这是阿伦特的著作给大多数读者的印象,这与新文献证据所揭示的那个自觉自愿的“狂热纳粹”形象相当抵触。
里拉说,阿伦特当时掌握的只是相关文献的极小一部分。如果认定阿伦特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而且认定她考虑了这些证据之后才得出艾希曼“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的判断,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就会让阿伦特“显得更为愚蠢,甚至超过她最尖刻的批判者所以为的程度”。伯科威茨的这种辩护会适得其反。实际上,每个人都会犯错,连阿伦特钟爱的圣·奥古斯丁也是如此。
通过介绍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以及他们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理解阿伦特是一件困难的事。她的概念和她的理论总是让我们处在一种不确定当中。
好了,这一次加餐就到这里。最后,如果你有什么感想和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到我的知识城邦留言。这些加餐最初是在知识城邦发布的,我把这一讲加餐的原始链接放在了文稿最后,点击进入原始链接,你还能看到同学们之前的讨论。
我们下次加餐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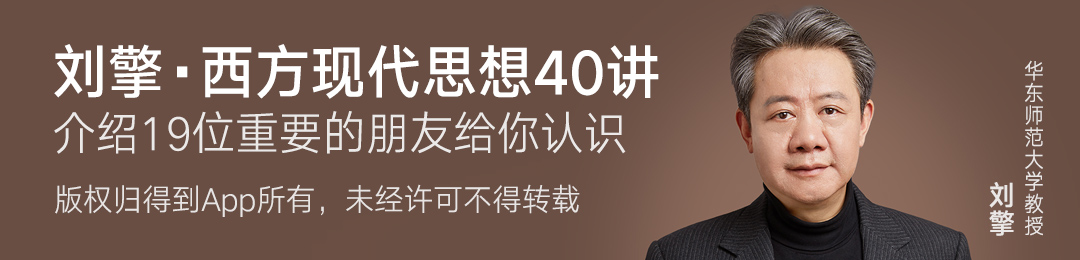
热门留言
淸风徐来:学习加餐,对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有以下几点理解:
第一,让我给平庸之恶下个定义。平庸之恶是类似艾希曼这种有文化、有教养,甚至是“值得人们尊敬的”的一类人,在所居体制环境内所犯的,看似有品行实则无品行,看似有觉悟实则无觉悟,看似有独立道德判断实则无独立道德判断,看似依法合法,实则突破“道德正直”这一人性大法,只知顺从,却不能真正反思自我的无知之恶。
第二,之所以敢下此定义,因为我觉得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原因基于两点,一是艾希曼就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反对者不会认同)并有其他人的存在,二是现实中无法证明这类人的不存在。
第三,艾希曼被捕之前所写的回忆录里的大段独白,骄傲地谈论自己“为了我的血液和我的人民”去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责备自己“应当做的更多”,并为“总体灭绝的想法未能全部实现”而感到遗憾。这不仅证明他是一个“狂热的纳粹”,而且也同样证明了他对“恶之平庸”的无知或故作掩饰。我看到这些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一个人仅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多么的可怕呀。
第四,阿伦特“平庸之恶”给我们带来的最震撼的启示是:自己若是艾希曼或处于他当时境地中会如何思考又会如何行动呢?这让我又想起了王阳明的“致良知”问题,恐怕我们在实际处境中,首先应该做到的是“致敬”良知,然后再去拿出良知的尺度。
有上述几点考虑,我还是十分认同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观点的。因为人性的良知就在每个人的内心,把握现实中的是非对错、真理谬误也许就在一步之隔。
佘天俊: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平庸之恶”的判断,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究竟艾希曼本人是伪装,还是无能,并不是阿伦特思想的精华,“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本身才是重点。 阿伦特提示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警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陷于“平庸之恶”。当潮水经过,随波逐流可能会导致极大的恶。 里拉纠缠于对艾希曼个人判断的正确与否,有点不够优雅。
Sofe:人们记忆中的艾希曼是一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还时不时帮助邻居修各种器械的“暖男大叔”。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他既不是这场屠杀的编剧、也不是它的导演,更不是它的制片人,他只是其中一个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演员”而已" 。
1️⃣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的恶”。这种恶不需要思想性或任何“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 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是,“不假思索”。在她看来,无法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去执行一些命令,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他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然而,这个人却是漫长迫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如果跳出自己的身份碎片,从一个更高的图景去看待自己,会发现作为一个个体,的确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却杀了无数人。很大程度上,这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的画板画好,但当所有的画板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出现了。
2️⃣普通人的普通在于,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就“不假思索”地去执行了。
更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蒙昧,而是将他们相互连接的力量——巨大的、失控的权力。没有那个巨大的纽带,再多的螺丝钉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无法构成一台轰鸣的机器。“平庸的恶”背后,是“激进的恶”。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是比较有限的。
3️⃣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做“理性的无知”,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恰如其分。
意思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4️⃣恐惧只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诱惑却能造就积极分子。 在艾希曼的自述中,他似乎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公务员,被动而茫然地执行着命令,“不知不觉”犯下了罪行。果真如此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权力向社会撒下利益的诱饵,他是努力跳起来去够那些诱饵的人。
1932年,纳粹党赢得大选之际,艾希曼即刻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1934年,他又加入党国的安全部门。这都是他主动的选择。之后,因为工作积极、表现出色,他不断获得升职,成为整个帝国“犹太人事务”的第一执行人。到最后,党卫军的“犹太人事务管理办公室”直接被叫做“艾希曼的办公室”。
比职业升迁带来更大满足的,是心理上的成就感。26岁加入纳粹党之前,艾希曼可以说一事无成,加入纳粹党后,由于其位置特殊,所以权力巨大。当时的犹太人团体,是走是留,如何走,如何留,走到哪,留在哪,他具有生杀予夺之权:他决定着逮捕或者释放谁,取缔或者放行某个机构。 从1939年开始,艾希曼成为“犹太人的沙皇”
这是何等的光环,一个33岁的年轻人,一个签名,一句话,决定着无数人的命运,而仅仅是在7年前,他连一份推销员工作都无法保住。所以,哪怕战争结束,逃亡到阿根廷,他依然沉浸在昨日辉煌中。最后,他之所以暴露自己,被摩萨德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向当地人炫耀自己是谁。在一张送给朋友的照片背面,他郑重其事地签名道:阿尔道夫·艾希曼——党卫军军官(退休)。
5️⃣ 所以,艾希曼绝不只是被动的螺丝钉,“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人。他是高高举手要求成为螺丝钉、主动跳进那个杀人机器的人。在法庭辩护中,艾希曼从不谈论他如何把自己放到执行人的位置上去,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艾希曼的恶,不仅仅是“平庸之恶”,而恰恰是“不甘平庸之恶”。
Edmund:看完里拉教授和科尔伯茨教授的争论,我产生一个问题:人性之复杂是否可以被洞察和理解?艾希曼身上到底有多少我们理解的艾希曼?艾希曼对他回忆录中的心路历程的描述是自觉的吗? 如果阿伦特对“恶之平庸”的阐释给我们一把深入人性洞穴的探照灯,那么这把探照灯发出的光可能是“思考”吧,可能争论的的焦点指向不在于“恶之平庸”这个概念本身多复杂,而是人性本身太过复杂了。自从祛魅时代来临,人性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抛给了我们自己的理性,这是极大的充满危险的考验。
Yuyang:阿伦特对恶之平庸性的分析,可能解释她面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但那不是实施了积极自由而不是仅仅因为官僚身份不得不参与屠杀的艾希曼。 不过我觉得阿伦特提出的问题更重要。为什么受到良好教育、具有道德感的普通人(没有陷入宗教之类的迷狂),会 做出这种不以人为目的也不以人为手段的行径呢?恶之平庸性、麻木性,是如何造成的呢?我们什么情况下会把非常行事“合理”化?为了生存,像那个被电击实验里的狗一样习得性无助?因为新的“信仰”,理性描述的允诺金灿灿幸福的新世界?
为光:我反倒是觉得,艾希曼在回忆录中的狂热性,正表明了他的恶的平庸性。阿伦特不是被艾希曼的平庸面具给骗了,恶的平庸性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浅薄,一种完全的不思考。艾希曼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是为了自己的血液和人民,去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这难道不是因为完全的不思考而被培养出的最坚定的信仰吗?
深海:《恶从何而来》书中说到有三种恶人,其中最危险的恰恰是第三种恶人,即怀揣着一个自认为高大的理想去作恶的人,他们不能说没有认知失调,而是把认知失调自我合理化了,所以他们往往又是很理性的人,理性不到不能阻止他们作恶,反而加强了他们对恶的合理化和恶的执行力。 如果说到艾希曼属于哪一种恶人,恐怕他不完全属于第三种恶人,应该是第四种,即“跟随第三种恶人的恶人”,他们不是领军人,但是他们确实放弃了思考,他们一样会将自己的行为自我合理化,这足不足以对其恶进行辩护?确实是个不容易说清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仍然有罪,罪恶原点在于懒惰和恐惧,因此他们放弃了思考,随之造成的恶果似乎不是他们主导,但确实是他们参与。 因为懒惰和恐惧放弃思考,这种恶算不算“平庸”?
吴运全:里拉的观点:能不能从艾希曼的回忆录所反映的极端观点中还能得出艾希曼是因为平庸,是因为没有自已的思辩能力,缺乏对别人的"恶"分析判断,所以坚信并且践行,这是阿伦特主观得出来结论。伯科威茨的观点:即使有回忆录为证,也只能证明艾希曼对别人的恶缺乏分析判断,还是一种平庸所致。这其实他们两个(或者说三个,包括阿伦特)都在事实、观点、信仰的框架内争论。每一个人都先从自己预设信仰出发,里拉的预设信仰是人性恶,而阿伦特和伯科威茨预设信仰是人性非恶而是后天蠢。其实从他们的争论方式来看,都先有一个信仰预设,然后用事实加工证明出来一个观点,有这个预设做为“暗环境”或者是“背景”,好象他们的加工证明逻辑自洽,结论正确。问题出来了,预设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可不可以更改?“暗环境”或“背景”很重要,往往被勿略或不被发现,这是我们更应该时时警醒的地方。
Bruce:那些我们熟知,甚至习以为常的是否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前提,我们进行正确的行动的几率是否大打折扣?重新发明轮子可能是可笑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和脑子的知识,特别是在那些变化巨大的时候。
许晓萌:如果任务目的是解释平庸之恶,那么他们会吵上一万年,直到时光机被发明他们回到过去找到同一个宇宙下的阿伦特——之后发现还得吵一万年,直到所有人的大脑全部、彻底、无死角地联系到一起。 如果目的是解释阿伦特已经成文的思想,那么或许任务会轻松一些——但有的人会把文字和一个人的生平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必定带有主观理解,那么他们不得不等待两万年,直到所有人的大脑全部、彻底、无死角地联系到一起,包括联系起来阿伦特。 哲学思辨(普通思考也一样),需要先有一定的、对基本词义和讨论问题的基础共识才能进行下去,然而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觉得,里拉和伯科威茨的争论几乎是鸡同鸭讲。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全面了解他们之间的全部争吵。 如果这种思考、争辩能为我们带来一点点新鲜的小火花从而引发更有深度的思考和具有意义的行为,那么即便吵不明白也无所谓。 所以总归,看到这种争论是好的,至少会引发我对于此的思考,从而写下这些文字——打出这些文字。
Sencer:今日思考,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只所以被人们接受,正是因为有了阿伦特这部著作,现在有了一些新的观点,说明一个概念从提出到论证,还是需要有时间与实例来验证。当一个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就有先入为主臆断的可能,对一些与概念相似的事件去进行评判。 一个人只所以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与他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来看一下艾希曼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他并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什么,而是认为自己是在为本民族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判断,才让他更忠诚于自己的工作。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在本岗位中,只知道服从,专心为了完成工作的人有错吗?当时的艾希曼不就是以这样的状态工作的吗,在当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他们有多少选择的权力呢?现在来看,仅用平庸之恶来对看艾希曼们的行为,好像缺乏说服力。 那么艾希曼的行为又给今天的人们有什么样的警示呢?当所有的声音都向一边倒的时候,我们又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到那个时候,恐怕也会以自保为主要选择。人总是会有趋利避害的偏好,那些真正服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在善与恶之间敢于选择用善行去对抗那些恶,这就是平庸的人不具备的勇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艾希曼并不是平庸之恶,而是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判断。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屠杀犹太人,并且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在他眼里,那些犹太人不是像他一样的人,而是一种标签和符号。他认为自己是在消除一种符号和标签,这些标签和符号就是纳粹所宣传的自私、冷血、贪婪,劣等生物,当这些标被他接纳,毁掉这些标签对他来说也就不会有什么罪恶感了。
Yasion姚延勋:个人感觉在这种多角度思想的对撞下,阿伦特观点的对错已经不再重要,艾希曼这种行为的底层逻辑会逐渐浮出水面,并一点点为我们揭开 个体人性中的纳粹 和 群体社会中的纳粹 是如何满足了哪类人的哪种心理需求?纳粹在什么条件限制下解决了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并又引发了什么新的问题?
朱家乐:我认为争论艾希曼究竟是否是平庸之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除非提出论证的人能够会读心术,不然就没法真正做到知晓大屠杀期间的真相,那就永远只会是艾希曼自己的一面之词,没法论证是真是假。
我们更应当做的事情是立足于当下,从纳粹德国的系统性残酷里好好学习历史教训,合理建设社会的顶层制度,防患于未然。这才是人类对二战最好的反思!
深海:刘擎老师好,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种问法:“对于平庸之恶,应该给予什么罚?” 对于怀揣或者跟随一个自认为伟大的理想作恶的人,如何定性其恶,目的在于给予什么样的罚,我觉得关键在于区分“常态”和“变态”,怀揣或跟随伟大的理想是常态还是变态,我个人认为是变态,因为伟大的理想并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支配其情绪和思考的,他们在常态中是能够感觉到其行为的恶的,只不过他们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变态”去将其自我合理化,所以这么说的话,他们仍然是选择了作恶。 所以如果把这当成一个法律或者伦理的问题,对于此种人的作恶给予罚,是完全正当,无可辩驳的,若非如此伦理和法律就丧失了可操作性。当然这仍然会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淡色的天堂:我觉得人更多的是情境动物不同情况下会说不同的话,所以艾希曼在审判时为了脱罪说的话很可能是谎话,所以阿伦特被他的话语和行为误导也是正常的,但是这不代表阿伦特就完全错了。艾希曼给自己辩护时说他是服从命令的,即使他就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自己内心并不这么想但是他这么辩护就意味着他认为人们会接受这一说法,也就是说这种说法在旁观者眼中是有合理性的,那么这个合理性从哪里来的呢,服从命令做了恶事就能被理解能被免除罪恶这个观念从何而来呢,说白了这还是一个现代化带来的观念,所以阿伦特还是洞察出了现代化带来的某种特点,这个特点导致了现代有太多“平庸之恶”,艾希曼是虚伪的并不影响“平庸之恶”是真实的。
Alex(钟前):思想的魅力在于思想的交锋。 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脱离这语境,我怎么能理解“过于复杂的简单"呢? 谢谢
大胡子:一个人犯下了在我们眼中难以原谅的错误。 我们如何去看? 表演理论中有一个好人意识我很喜欢,就是说不论这个人做什么,都是带着我是好人这个意识去做的,坏人也不是说我就要做坏事。
就像最近很火的网红周某,把不劳而获,偷电瓶的行为说的冠冕堂皇,打工是不可能的,这类金句反映出了他的目的和好人意识。
所以平庸之恶,他也有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