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路标:现代人为什么会遭遇精神危机?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和我一起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板块: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又叫信仰危机。
关于这个主题,存在主义思想之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说, 在信仰问题上,我们唯一的选择只有鼓起勇气“纵身一跃”。
为什么要纵身一跃?要跃过的是什么?又为什么需要鼓起勇气?
明白了这句话,你就会理解“信仰危机”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在拜访接下来几位思想家时,你就会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思路。
“终极关怀”追寻的到底是什么?
在讲解理论和思想之前,我想先给你念一段话,请你沉下心来听:
“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于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
这段话来自克尔凯郭尔22岁时写下的日记。不知道你22岁的时候,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呢? 对于人生意义这类问题的思考和关切,其实就是哲学家说的“终极关怀”。
不过,别以为终极关怀只是哲学家的课题,这其实是一个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设想,当你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你想要问自己:“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
答案可以有很多,“为了家人”、“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等等。说出一个具体的目标并不难,但如果要问这个具体目标有什么意义,就需要更大的目的。如果一直追问下去,就会遇到那个根本问题: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终极关怀之所以“终极”,是因为它追寻的是所有答案的答案。 要给出这个答案,你得有所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
也有人会说,干嘛非得要追问什么意义呢?我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不需要问那么多。的确,即使不去想什么信仰、意义,我们或许也能过好日常生活。好像能够避开对根本问题的追问,这就解决了信仰问题。
可是,真的能回避得了吗?
无法回避的两个难题
许多哲学家认为,这只是假装解决了问题。 信仰问题就像一个幽灵,总会在某个时刻与你不期而遇。因为人在精神层面需要面对两个巨大的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
先说死亡。死亡是一个重大问题吗?也有人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古希腊有位哲学家伊壁鸠鲁说:如果你在思考死亡问题,就说明你还活着,既然活着,就没必要操心“死”的问题;等到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死亡”就不再是问题。你看,按这个说法,操心“死亡”这件事,根本没必要。
“没必要”就能终结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不能。虽然我们现在活着,但人能够意识到死亡。我们知道死亡是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残酷,它是会终结其他所有可能性的可能性。“人终有一死”,这没错,但人的意识中还有“永恒”这个概念。这二者的对比会在人心中埋下一种深刻的悲哀,所以我们会哀悼逝者,也会为自己的死亡而忧虑、而恐惧。
另一个问题则是“贪欲”。人毕竟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会有一些原始的、动物性的欲望。但同时人又是精神性的存在,我们有良知、有道德感。动物性的欲望时常会与良知和道德感发生冲突。 就像“人终有一死”和“永恒”的对比一样,原始的欲望和“崇高”也形成了一种对比。 这种对比会让我们觉得羞耻和不甘,严重时甚至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卑微。
你看,死亡和贪欲给人在精神上出了两大难题。终极关怀其实就是要应对处理这些难题。怎么应对呢?一个典型的解决方案是宗教。比如基督教中讲“灵魂拯救”,说肉身虽然会死,但灵魂能够永生;虽然凡人都是卑微的、有罪的,但信仰虔诚就能够达到崇高的境界。这是宗教的方案。
非宗教的人生理想也是一样。我们小时候学习雷锋,他有一句名言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你看,这也应对了前面说的两种困境:把生命献给一个无限的事业,短暂的人生就找到了永恒的归属。这也指出了一条通往崇高的道路,只要在这条道路上攀登,就能超越个体的卑微。
我们看到,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人生理想,都能为死亡和贪欲问题给出处理方案。那问题来了,既然方案就在这儿,很明白,为什么还会有信仰危机呢?
“真实”与“信仰”之间的裂痕
答案是,信仰危机来自于一道裂痕,是位于“真实”与“信仰”之间的一道裂痕。
就拿宗教的例子来说。过去,宗教在思想上和社会现实中都被广泛接受。那时,信仰宗教是一个默认的选择:在精神世界,宗教代表着神圣和正道;在现实世界,大多数人都信仰宗教,是社会的主流。
但是,当历史跨过一个节点,这种“默认”地位被打破了。这个节点就是之前讲的“古今之变”。古今之变后,信仰遭遇到理性主义的挑战。 人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事物要求我们相信它,那么它应当证明自己是真的、可信的。 人生信仰的意义如此重大,更需要证明它的可靠性。对现代人来说,这顺理成章。
但是如果你坚持要把“信仰”和“真实”统一起来,那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人生信仰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呢?一是对于永恒的许诺,二是对崇高的指引。那我想请你回忆一下之前讲过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请问,判断“什么是崇高的”,你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
很显然,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请注意,裂痕已经出现了。我们一步一步看这个推理过程:
首先,信仰是一个价值判断;
其次,现代人对信仰的要求是“必须是真的、可靠的”;
可是,“是真是假”,这是事实判断的评判标准。
这就是我所说的“裂痕”: 在信仰问题上,人们在用审核事实判断的标准,去审核一个价值判断。 这就像是用短跑比赛的快慢标准,去评价一幅画美不美,是行不通的。用学术语言说,就是 “信仰”与“真实”之间的逻辑断裂。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为这个问题纠结了一生。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无法依靠逻辑和知识来确认信仰是否是真的,只有勇敢地“纵身一跃”才有可能越过这道鸿沟。 这其实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能知道这一跃的结果是到达彼岸还是跌入深渊,连计算这件事的概率都做不到。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要纵身一跃?是 因为单凭理性达不到信仰的彼岸,只有纵身一跃,才有可能跃过知识与信仰之间的鸿沟。这一跃的后果不可预知,前面可能是拯救,也可能全是虚空。这完全是一种冒险,需要极大的勇气。
当然,克尔凯郭尔的论断针对的是宗教信仰。但我们看到,他描述的,其实是每一个追问人生意义的人都会遇到的困境。就算你选择的人生信仰和宗教无关,也是一样。
比如,登山者把登山当作自己的信仰,记者问他为什么要登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可是这个回答经得起理性的考问吗?理性能够证明,登山是一件伟大的、有价值的事吗?选择这个信仰,实际上也是一种“纵身一跃”。但更痛苦的是,许多人甚至连目标都没有,也不知该“跃”向何方。这就是现代人要面对的信仰危机,或者说精神危机。
答案并不绝对,思想总有启发
总的来说,人总会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而终极的追问总会遇到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要应对这两大难题的挑战,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人生信仰。经过启蒙理性主义的洗礼,现代人更倾向于根据理性来确认或者求证信仰的可靠性。但是,在理性和信仰之间有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结果就是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处境,就是我们这一板块的主题,“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也被这个问题困扰,那么你不孤独。人类历史上有一些最了不起的头脑,都思考过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的答案并不是绝对的,但我们能从这些回答中找到对自己的启发。
接下来我们要拜访的,就是三位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洞察的思想家:尼采,弗洛伊德,萨特。首先是尼采,那个喊出“上帝死了”,震撼了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德国人。下一讲,我们继续。
问答讲完了这一讲,我很好奇,你是否也思考过人生意义的问题呢,当时你给自己的回答是什么?很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划重点
1、终极关怀就是对于人生意义这类问题的思考和关切,它需要有所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
2、信仰问题就像一个幽灵,总会在某个时刻与你不期而遇。因为人在精神层面总要面对两个巨大的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
3、在“信仰”与“真实”之间有一个逻辑断裂,我们无法依靠逻辑和知识来确认信仰是否是真的,只有“纵身一跃”才可能越过这道鸿沟。这一跃的后果不可预知,需要极大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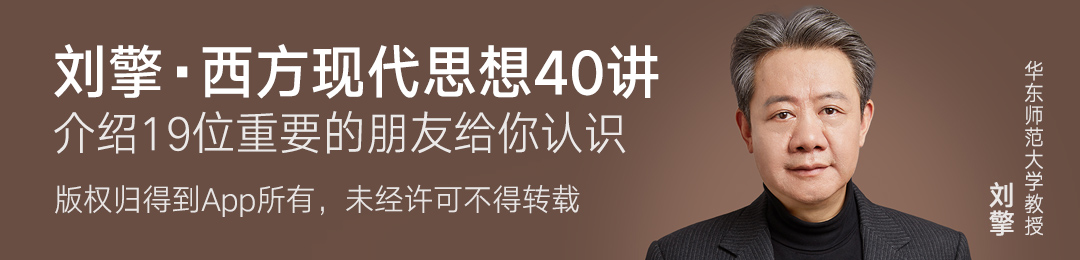
热门留言
徐建航:人生的意义不是问出来的,也不是回答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
刘擎(作者) 回复:太棒了!“活出来的”可以是一个回答。但如何活出来呢?就是行动,是实践,但行动之中包含“问”和“答”吗?
许晓萌:我的想法如下: 人难免一死,我不惧怕死亡,甚至会在有些时候期盼死亡到来(抑郁的时候,身体内分泌失调的时候)。 所以我不在乎死亡,因为这非我所能掌控。但我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质量,所以我要健身,我要克制,因为我会在健身和克制之后产生巨大的愉悦和满足感。 同时,我有我的追求——我想读更多的书,我想了解更多的知识,我想变得富有,这样我就有时间去健身、读书和过我想要的生活,然而金钱只是做对事情的副产品,所以我不可以本末倒置,于是我要先健身、学习和乐观生活。 我还有了家庭,我爱我女儿,所以我要比一般人更好,因为我希望自己成为最卓越的那一类父亲。 我还希望活得更久,因为我想知道人类到底能够达到多么高的高度,想一想这个问题,实在是令我兴奋。 我不在乎什么意义,我只知道,做这些事让我满足,并且我深知,当我陷入痛苦的泥潭无法自拔的时候,如此上进的我只需要配合一些多巴胺等药剂的使用,就又可以再次充满活力,直到死亡降临。 我是一部特殊的机械设备,我尽全力维护并满足它的所需,因为这会让我快乐。快乐,是动力之一,这就是我此刻能够想到的我的全部的对于生命的想法。
星空:自从我理解到人可能没有自由意识时,我就一直在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能生命不存在什么意义,但理性让我不能接受这一事实,最后我妥协认为生命的意义是各种体验的总和。
刘擎(作者) 回复:人有没有意识,有没有自由意志,而且意识是什么,自由意志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无论如何,你意识到你可能没有自由意识,而且因此给了自己一个“妥协”答案,这是就是很有意思的生命意义建构啊。
佛祖门徒:《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小书”曾经带给我重大的启发。常听人说中年危机,也有人抱怨自己活在别人的眼中,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每个人都希望借此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无论是书中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还是后来开创的“意义疗法”都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人活着就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在集中营里,有一种折磨就是纳粹让犯人周而复始地挖坑、填坑、再挖坑,于是很多人崩溃了,因为他们找不到这种重复劳动的意义。 哲学家思考“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呢?”这个问题让我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思考和反省,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我凭借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能够给这个世界创造什么价值?我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当我时常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明白有些问题自己无法找到答案,但是有些问题我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去努力回答,比如我能够创造怎样的价值?我该如何体现人生的意义?不妨问自己一个命题:一个世界有我,一个世界没有我,我能够让两者之间的正面差异最大化就是我创造的价值,也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常常在想,当我有一天死去,人们会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下一句怎样的话来概括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是对自己一生最好的诠释吧。
金戈铁马:在现代社会,支撑个人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价值判断,而现代的科学知识,则是属于事实判断,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无法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由此,在个人层面上,就带来了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无法获得逻辑推理、或者理性论证的担保。正如韦伯所言,“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这就有可能导致抑郁症;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立场,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却又可能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所以,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并没有标准的解决方案,还是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亲身实践,摸着石头过河,去探索属于自己的答案。
重庆Franklin:刘老师好 这里的“纵身一跃”到底啥意思呢? 裂痕来自用事实判断去验证价值判断,这是行不通的。所以正确的方式是用价值判断去验证价值判断,也就是不需要理由的完全相信信仰,这就是纵身一跃?这样理解对吗?
刘擎(作者) 回复:好问题,我会在知识城邦的小加餐中回应这个问题。谢谢!
陈C:从这一讲得到的启发是,克尔凯郭尔说要“纵身一跃”去越过的鸿沟,其实是一种错位,是用事实判断的方法,去给一个原本该交由价值判断的事情下定论的时候,必然会遭遇到的窘况。但问题是,既然存在这种用判断“真假”的方法去审视“高低”、“好坏”的错位,我们又为什么会执迷不悟呢?我认为原因主要在于两点: * 第一,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化进程让我们习惯了先定真假,再去相信,因为这样能带来更具确定性的依据,为后面的判断打下更好的基础。这就像是“手握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一样,即便面对的不是钉子,也是会下意识敲一下的。 * 第二,是进行价值判断本来就很困难。理性化带来了好用的思考工具,却也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再多的参考标准也可能有所遗漏,标准之间孰先孰后也令人困惑。而为了简化思考,即便不合适,事实判断的工具也可能会被强行挪用过来。
我并没有深入思考过人生的意义,只是涉及了一些衍生问题,比如“我应该为什么而活”、“我应该以什么为事业”等等。当时虽然不了解事实判断的工具,与价值判断的目标之间的错位,但想着想着,倒也想明白了这样一些事情: * 应该为什么而活,似乎并不是一个能够用逻辑与事实证据来证明的问题,倒更像是一个“应不应该”和“适不适合”的问题。 * 既然谈到了好坏与适合,那么其结果一定是主观的,并且因人而异。 * 既然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每个人的答案就终归只能他自己去寻找,别人给的路再好走,也不一定是自己该走的那一条。 * 以我有限的知识和阅历,还看不到自己应该走什么方向,也许应该沿着脚下的路先走着,说不定走着走着就看到方向了。
想来想去,当时的结论就一条,先好好活着再说,路都是脚下走出来的。
金戈铁马:我个人的观点,人生也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感性阶段,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理性尚不成熟阶段,一般都是从我们出生到大学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较少,所以典型特点是热血、冲动,只凭自己的热情去做事,但不太会考虑事情的后果或者是需要承担的代价,也常常会惹祸。第二个阶段是思想的成长期,这个时期通常都要经历很多的痛苦和迷茫。一方面,我们逐步进入社会,开始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互动,也被要求按照社会的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来约束我们的言行。同时,我们也会面临各式各样的考核和抉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对自己的思想产生困惑,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也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我们都是在与社会的互动和实践中,不断摸索人生的真谛。第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人生的成熟期,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逐渐衰老,但精神世界却愈发的成熟,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超越理性、掌握人生存在的意义。我们逐渐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能够做到深思熟虑、处事得体,平衡好自我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自己和他人的交往,并且能够乐于将自己的所得传承给下一代的人。当然,第三个阶段的实现,需要以第二阶段的大量实践和思考为基础,通过大量的积累才能达到。
斜阳:思考人生意义是每个人都躲不过去的,为什么要纵深一跃,除去逻辑裂缝,具体人生本就是不连续的,有很多十字路口,过多的思考最后只有两个结局:要么停滞不前,要么面对虚无。所以,行动往往才是自我迷失的解药,纵身一跃是必然结果。功夫熊猫里面有句话,我在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经常会想起,Yesterday is history,Tomorrow is a mystery,but Today is a gift. 大多数人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是找到生命的意义,但是从神话里体会人生的坎贝尔却认为,“你真正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生命体验”,过程体验本身就是意义,我个人目前最认同这种解法。
徐徐:小的时候偶尔会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到底没有深究。真正直面这个问题,是26岁那年,我最好的朋友病逝。 以前也有经历长辈去世,但都不如好友去世对我的打击来得大。身为医学生,自以为看淡生死,但是,当一个与我关系亲密的,一起描绘未来美景的,年轻的,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的时候,死亡的力量深深震撼了我。 我开始反思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既然人都有一死,一切终归尘埃,我们忙忙碌碌一生是为了什么呢?我开始寻找这个答案,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有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让我不再被死亡震慑。 一是《三体》系列小说。里面有很多关于人类命运与个人命运的探讨。从宇宙社会来看,人类其实与朝生暮死的蜉蝣没有区别,客观世界并不关心人的生死。看完之后,再大的问题,我都可以淡然处之:又不是三体舰队来了。 二是《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我不确定自己有正确理解作者对于自杀的探讨,但我学会了正确看待死亡这件事。个体是否拥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这个问题很有争议。选择死亡需要勇气,选择活着也是。至少承认这个权力,能给活着的人多一点底气。 我会问自己:既然找不到生命的意义,那如果此刻就死去,你愿意吗?——我不愿意。虽然现在还没找到答案,或许终我一生也不会有答案,但我在寻找答案的路上,不想放弃。
自然联盟:我听过王立铭老师讲过的生命科学课,人是有意识的,但没有自由意志。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王立铭老师的生命科学中已没有给出答案。我个人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个体的体验,象科学家等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具大贡献的,生命可能有意义,而普通人,生命则无意义。都不就是基因的延续吗?若有不当见谅。
刘擎(作者) 回复:个人的体验是一个回答,但本身又可以变成问题:什么样的体验才有意义?。人类进步为什么是意义的衡量标准?如果认同这个衡量标准,那么普通人也在做贡献,生命也有意义啊。
钟敏:在我的日记里写过这样的话,人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就像是一块煤,静静的在山里风吹日晒,有一天被开采被放进火炉里,他在那一刻得知自己的意义就是燃烧,散尽所有光和热,他会开心地拼命燃烧直到成为灰烬,虽然短暂但是完成了终极意义的幸福感已经超过了风吹日晒千年。
辣条龙:之前经常思考却不得其解。
最近有些焦虑,试着冥想,童老师有一句打动我,冥想是觉察当下,觉察自己,不是做更好的自己,而是更好的去做自己,我想,这会是我近几年生命的追求吧。
前几天邵恒推荐的少年时代电影中,父亲对儿子说的那句话挺触动我的:生命其实就像一场即兴表演,谁也不知道意义是什么,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认真的去体验、去感受这个过程,并一直用心感受下去。
骑大鹅:这节课的设置非常棒啊,不是直接讲三位大师的思想,而是提出问题,做了个过渡,课程体验非常好。
自由飞翔的鱼:请问老师,像牛顿这样的伟大科学家他怎么把信仰和工具理性统一的?
刘擎(作者) 回复:他生命最后几十年都在追问上帝存在的问题
静静:人生意义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会去寻找,有些人会很幸运,知道这一生要怎么过,而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身心安顿。我想追寻意义的过程也许就是人生的意义。
刘擎(作者) 回复: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就说过类似的话,美好的人生就在于对美好人生的追寻之中。
是李亮: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由来以久。 1、在伟大的Augustine之前便有一位教父哲学家Tertulian,他表示正因为荒谬,所以才信仰。 2、Augustinian学派的态度基本一致,信仰高于理性。他们说:信仰以求理解(Credo,ut intelligiam;I believe,so I may understand)。 3、到了St. Thomas,他划清理性与信仰的界限,因而神学与哲学各有自己的地位。 4、近代的帕斯卡提出一个“赌注论证”(wager argument)来支持信仰。大意是说无论上帝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信仰他:如果他不存在,我们也不信仰他,这没有任何影响;如果他不存在,我们信仰他,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如果他存在,我们不信仰他,我们注定损失很多;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上帝存在,并且我们信仰他,我们可能得救。四种情况里面,显然选择信仰比较合理;不过这种态度也遭到批评,原因是过于考虑利益关系。 5、休谟是出了名的怀疑论者,信仰被质疑自然不在话下,可是什么是确定的呢?他似乎也没有好的答案,他最终也只能说:我们只好按着传统和习惯生活。 6、许多哲学家试图rationalize(理性化)基督教,比如著名的John Scotus Eriugena和Hegel;近代西方也兴起了demythologize(去神话化)的热潮。 …… 我当然不认为普通信众也考虑了这么多,而只是想强调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问题由来以久,各路高手也都试图给出他们的解决办法,尽管一些办法看来也不是很高明。
佘天俊:越来越喜欢刘擎老师浑厚安静的声音了。 这集的“纵身一跃”有种惊艳的美,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克尔凯郭尔22岁那句话,简单的说,就是“人终究该相信点什么”,而什么是那个什么,就像韦伯的价值理性,应该是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但问题在于,这每个不同的标准无法获得反馈和认可,甚至在外界遭遇反对和不理解。 安全的做法是,做一个大家都做的选择。这导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合二为一。不知道这是不是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原因之一。 伊壁鸠鲁把死亡当做瞬间动词,而人面对的死亡,是一个持续过程。重要的并不是死亡时刻,而是死亡之前,我们怎么看待死亡,怎么面对死亡,怎么在死亡的阴影下调整自己的行为。 至于贪欲,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贪欲并不是动物性的。原始动物本来,由于无法储存事物,有贪欲也是种有限贪欲,而人类创造了储存,创造了财富,创造了金钱,导致无线贪欲的可能。 “首先,信仰是一个价值判断; 其次,现代人对信仰的要求是“必须是真的、可靠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裂痕”:在信仰问题上,人们在用审核事实判断的标准,去审核一个价值判断。" 这真是一个精彩至极的推论。 纵身一跃,简直绝美。
刘溜溜:人总会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而终极的追问总会遇到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要应对这两大难题的挑战,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人生信仰。
想想我自己,好像慢慢长大之后,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问自己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比如读书有什么意义;考上好大学有什么意义;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下去吗等等。要问我自己的人生信仰是什么,似乎我也回答不上来。
现在我们常说要找到人生的使命,这个和人生信仰很类似,只是我们该如何找到人生信仰是个问题,找到了之后它真的对我们来说是否有意义又是个问题。老师在这节课中提到的“纵身一跃”,我就把它理解为要行动起来,判断自己的信仰,不是靠思考和计算,而是真的去尝试,在行动中感悟的。起码,行动时有方向,就是一件好事。
云云起:集中思考生命意义,好像有三个时期:一是十几岁的青春期;儿是刚刚回国的时候;第三次就是18年年底。 我曾经在18年底一度抑郁,因为看不到生命的出口和方向,感觉一切都无可无不可,甚至一度过激到想放弃人生了。之所以没有选择极端,是因为舍不得妈妈,觉得还没能尽孝。后来慢慢走出那段困境,是通过读各种各样的经典、小说,哲史,慢慢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宏大的维度去感受,心也就慢慢打开了。现在,重新找到喜欢的演员,追剧,发现生活新的热点。 最重要,现在,我觉得生命是一个过程,一切都是体验,不再那么执着去找一个特定的意义。
评论